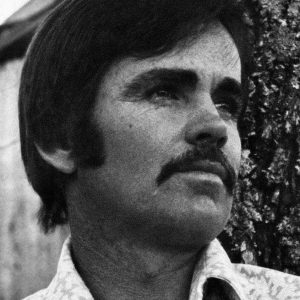保禄六世教宗于1964年1月4至6日赴圣地进行历史性朝圣访问至今已60年[1]。这个周年纪念正逢一段极其艰困的时刻,即巴勒斯坦哈马斯(Hamas)武装组织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突袭悲剧后而引发以色列对该组织的全面攻击。这个战事已导致许多人命丧亡,以方有1200人丧生,巴勒斯坦则有21000人生灵涂炭。不幸的是虽然双方近期达成短暂停战协定,彼此交换人质和囚犯,但战事似乎仍将进行下去。以色列政府声明战事的目标乃是从加萨走廊地区铲除哈马斯组织,尤其是这个组织的几位领导人,不论他们在何处。一如之前美国在发生2001年9月11日事件后,对“基地组织(Al Qaeda)”首领们采取的行动一样。保禄六世那次“受赞颂之旅”提醒我们和平的崇高价值,并必须始终予以维护,即使在此看似黑暗和迷失的时期也该如此。教宗方济各至今仍不断重提保禄六世圣地之旅,他恳切呼吁各宗教之间和各国之间和睦共处。
保禄六世教宗圣地之旅被史学者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宗教事件之一。这位教宗在当选不到一年,即开创有史以来第一位教宗走出欧洲旧大陆的壮举,他搭乘飞机旅行访问成了时代进步和现代化的里程碑。更特别的是,保禄六世乃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教宗前往基督信仰的发祥地:这是个具有呼唤记忆和必要之举;他随后的几位继承者也都步武其芳踪,在某些历史背景、甚至艰困的时刻,赴圣地朝圣。保禄六世以朝圣者身份参访了位于耶路撒冷和加利肋亚的一些圣地,会晤了当地东方礼基督信徒团体以及他们的宗主教。最特别的是身为罗马主教的他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大公宗主教阿特纳格拉(Atenagora)在耶路撒冷的两次会晤。这项会晤开启了罗马天主教与其他基督信仰教会团体的大公合一对话。东、西方两个教会最高牧人在耶路撒冷彼此拥抱的友谊之举加速完成了双方最具前瞻勇敢的行动,即在1965年12月7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之前,两个姐妹教会同时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和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宗主教驻地法纳尔(Fanar)举行弥撒圣祭,礼仪中宣布移除发生在公元1054年彼此绝罚的记忆。
保禄六世教宗在梵二大公会议期间和之后共进行了九次牧灵访问之旅。这些行程都是一番深入默想思考和理智妥善选择的成果:这都是保禄六世教宗意欲传达给梵二大公会议和现代世界的讯号。一般来说,他的这些行程虽然都不长,但其“一举一动”和所发表的感人讯息均深富热切、深远的意义,极具重大的象征价值:那是宣讲基督福音、与世界并肩生活的崭新方式。无论如何,蒙蒂尼(Montini)教宗也是透过他的“宗座牧灵访问”开创了执行伯多禄继承者使命的先知性天才先锋,他的创举为他几位继承者所广泛承袭,直至当今的教宗方济各。
筹备圣地朝圣访问之旅
1963年12月4日上午,梵二大公会议第二阶段会期遵照保禄六世教宗的期许,长时深入讨论教会的模式之后,教宗宣布他将于次年元月赴圣地朝圣访问,“为亲自瞻仰基督出世、生活、死亡、复活并升天的地方,默观我们获得救恩的最初奥迹”[2]。他随之明确指出此行的性质说:“我们将瞻仰那片受祝福的土地,伯多禄曾从那里出发,至今却尚未有过一位他的继承者回去过;我们将怀着祈祷、忏悔、做补赎以及革新的心情,极其谦卑并极为短暂地回到那里”[3]。
在展开如此一次极具政治、宗教复杂性之旅之前,这位教宗曾在几个机会上明确说明此行的意义。他在向枢机主教团和外交团致辞时,强调他此行不具“政治目的”,而是“宣认信仰之旅”;他又说“这将是祈祷和谦恭之行,一个纯为宗教性之举,与任何政治和世俗事务考量毫无瓜葛”[4]。这些都是保禄六世教宗纯真的宗教和心灵意向,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大公会议教长们所期盼的一次教宗赴耶稣家乡巡礼之行。的确,保禄六世教宗在做此决定之前,并没有获得约旦和以色列两国政府或宗教当局的邀请:他只愿意以罗马主教的身份前往,而非以宗教领袖或一国元首之尊前赴接受某种形式的欢迎。他说“我们将诚挚地向行程中遇到的任何类别的人士,特别是有关当局、人民、朝圣者及观光旅客致敬意,但绝不放缓我们的步伐,绝不忘却我们此行唯一的宗教目的”[5]。
保禄六世教宗圣地之行虽然非常短促,却也能亲莅耶稣在世生活最具意义的地点,特别是耶路撒冷、纳匝肋和白冷。根据某些分析者称,保禄六世为了准备他的行程,曾派遣他的幕僚帕斯瓜勒·马基(Pasquale Macchi)和贾克·马丁(Jacques Martin)两位蒙席前往中东,与当地民政和宗教当局洽商协调朝圣访问细节。但其他方面的人士则称,梵蒂冈仅派遣了几位官员到当地做了个简单的现场勘察,并未通知有关国家当局[6]。在此必须一提的是,当时圣地处于两个敌对国家的主权控制之下,即约旦和以色列;前者掌握耶路撒冷旧城区,后者则控制沿海、內葛夫(Negev)沙漠以及加利肋亚地区。那些地区的地理于三年后(1967年)发生的“六日战争“而完全改观,彼时以色列军队击败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军,占领了绝大部分的那片地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
此处理所当然该强调的是,在梵二背景之外,保禄六世的圣地之旅是无法想象的。从某方面看,那次朝圣访问之旅乃是大公会议所诞生的“果实”。藉着这个深具崇高象征意义的行动,教宗愿意引导大公会议教长们注意两个极重要的、深受会议讨论的议题:一个是万有所从出并赖以建立的天主圣言的根源价值;另一个则是实际上仍在孕育酝酿中的基督信徒的合一,至少教宗这么说,而“合一运动者”也这么认为。根据若瑟·阿尔贝里戈(Giuseppe Alberigo)的看法,保禄六世圣地之旅被安排为“一个具君主和首席地位性质的杰出之举”[7]:藉着此举教宗重新掌握公共场面,并因此以毫无模糊的方式肯定了教会一向认为的教宗首席权的教义。阿尔贝里戈这位史学者之所以这么认为,因为从保禄六世圣地之行全由梵蒂冈圣座国务院这个政治机构来筹划安排,而不是由此行必然涉及大公合一运动后果的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这个大公会议的单位来负责。事实上,这样的行动考虑或策略当然不在教宗脑海中,因为他绝不会做相反大公会议的事,也切望会议正常进行。
正如可以预见的,教宗圣地之行的宣布不但立刻引发舆论和媒体的注意,更引起国际、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美国外交界的关心。这次圣地之行,从教宗原先设想和提出的纯宗教性质,逐渐凸显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首先,在教宗启程之前,圣座已告知有关国家政府在政治上、尤其在以色列与其邻国的边界问题上,圣座保持绝对中立的态度,至于圣座对耶路撒冷的立场各国早已知晓,即:在国际的保障下赋予圣城以特殊的地位。同样的立场梵蒂冈外交当局最近也重申过。无论如何,保禄六世从未提到此行的政治面:他在与政治领袖们“仓促的”会晤中,仅仅谈及各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和平及共处共荣。
1963年12月8日以色列政府(部长会议)发表官方公报,对保禄六世教宗圣地之行表示完全赞同满意;但就如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在那几天向华府当局的报告中强调,圣座与以色列之间的岐见仍然重大,诸如耶路撒冷城的行政管理条件,该城维持现状的条例,以及所谓的庇护十二世教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境遇保持沉默等等。关于最后这个问题,在罗孚·霍奇胡特(Rolf Hochhuth)编著的舞台剧《Vicario(基督在世的代表)》在巴黎演出后,更具时事性。约旦国王胡塞因(Hussein)也对教宗之行发表了极为感激的话。事实上,教宗圣地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约旦首都安曼。这位自许为穆斯林圣地唯一“守护者”的哈希姆王国君主有意藉着教宗圣地朝圣之举,在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面前强化自己的地位。的确,他承担护送教宗一行人从约旦首都至耶路撒冷的安全任务,并且自驾直升机从空中伴随[8]。
黎巴嫩和叙利亚也适度地要求将两国同时列入教宗的访问行程,以示公平。黎巴嫩更以其为中东唯一基督信仰国家,拥有众多天主教徒、特别是马洛尼礼节(Maroniti)天主教徒,而且数世纪以来一直与罗马关系密切的理由,表示受访的希望。然而,据说梵蒂冈以为如果教宗前往黎巴嫩,可能会伤害那个地区基督信徒和穆斯林之间业已存在的脆弱关系,尤其担心教宗的车队从以色列国境开抵贝鲁特时的状况[9]。至于叙利亚,当时执政的是倾向俗世的阿拉伯复兴党(Ba´th),该党正寻求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所以也希望教宗访问大马士革这个全球基督信徒因圣保禄的缘故而喜爱的城市,但圣座谢绝这项邀请,因为教宗圣地之行必须保持其宗教性质,不给参与梵二大公会议的中东主教们和生活在那些地区人数既少又脆弱的基督信徒团体制造问题。
从宗教圣地之旅到基督信徒大公合一之行
保禄六世教宗宣布他的圣地之行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大公宗主教阿德纳格拉(Atenagora)闻讯后即通知教宗他渴望与教宗在耶路撒冷相会。这又改变了教宗圣地行的性质。这位宗主教说:“如果在保禄六世这次宗教之行期间,东方和西方教会领袖都能在熙雍(Sion)圣城相会,这该是真正天主上智安排之举”[10],为向上主祈求基督信徒合一的恩典。就这样,教宗之行又圆满地恢复纯精神和宗教的特征,甚至意想不到地丰富了基督信徒大公合一的要素。这原是教宗和大公会议所非常惦念在心的。
阿德纳格拉宗主教的提议很受保禄六世和他身边幕僚的重视。教宗立刻派遣一位专员赴伊斯坦布尔协商此事。但有关方面认为即使有这位宗主教的善意,问题仍有些复杂,因为这件事还得经过东正教主教会议的讨论和决定,而事实也是如此。埃及亚历山大和土耳其安提约基亚的宗主教宣布赞同这项会晤;而莫斯科宗主教则因为之前有关派遣东正教各教会团体代表赴罗马参加大公会议一事持不同意见,致使君士坦丁堡全东正教最高当局感到难堪。为了弥补这件不愉快的往事,于是不反对阿德纳格拉宗主教与保禄六世在耶路撒冷相会的创举。然而,最大的困难乃来自希腊教会,她固然表示赞同,却拒绝派遣自己的代表陪伴阿德纳格拉赴耶路撒冷。
因着这项消息的广传,各方对教宗圣地之行的重视与日俱增。这自然大大更改了教宗种种会晤活动的行程方案:事实上,保禄六世在耶路撒冷不仅要会晤天主教拉丁礼的主教们,也将会晤该城每位东正教的宗主教,特别是希腊东正教和亚美尼亚教会的宗主教。
耶稣在世生活之地巡礼
教宗圣地之旅吸引了全球媒体界派遣人员前往随行,实况全程报导,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一千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紧随教宗的活动行程寸步不离。这大大有助于世界舆论对中东宗教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和了解。1964年元月4日一早,教宗在罗马达文西国际机场向欢送他的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致谢后,随即启程。抵达安曼时,受到约旦国王的迎接。之后,在约旦国家警卫队的护送下乘车前往耶路撒冷,于下午五时许来到圣城,在满溢各种喜庆色采的气氛中从大马士革门进入旧城区,夹道欢迎的人群一时涌上前来,环绕在他坐车的四周,致使欢迎教宗的官方仪式无法依时举行,只好延后。为了避免意外,他坐车的门关闭着。慢慢地教宗好不容易开始沿着通往“圣墓”圣殿的窄长“苦路”(Via Dolorosa)亦步亦趋地前行,他几乎被人潮所吞噬。为了避免拥挤的人群,有五位士兵手握手在教宗身边围成一圈以保护他。教宗在人海中徐徐前行,时而可见,时又隐去,他虽然因疲乏和激动而显得脸色苍白,仍始终微笑地祝福群众。下午六时他进入圣墓圣殿举行弥撒圣祭。据教宗后来回忆,在圣墓奉献弥撒乃是此行最令他感动的时刻[11]。
之后,教宗在圣墓圣殿内颂念的祷词也非常感人:“主耶稣啊,请看,我们像罪人一样来到行凶谋杀的场所和受害者面前;我们来到这里乃为承认我们的罪过和你的苦难之间的神秘关系:这是我们的罪过,也是你的杰作;我们来到这里捶胸,祈求你宽恕,呼求你怜悯;我们胆敢来到这里,因为我们知道你能够也愿意宽恕我们,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补偿了罪过:你是我们的救赎,你是我们的希望”[12]。
元月5日是保禄六世此行的“以色列日”。这天上午十时前几分,教宗的车队越过圣座尚未正式承认的以色列国界。在梅吉多(Meghiddo)受到以色列总统匝曼·萨扎尔(Zalman Shazar)的欢迎。他致词说:“以最真诚的敬意和完全意识到这件盛事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历史意义,我在此谨代表以色列政府和我个人向最崇高的教宗阁下致欢迎之意”[13]。以色列总理和这个国家的大经师并没有出席这个场合,但在当天上午他们已发表公开声明,推崇教宗此行。教宗的致谢词即使从未提到“以色列国”,却非常感人,他说:“从这块曾经是史上伟大事件剧场的世界独一无二之地,我们为全人类,不论有无信仰,向天主谦卑呼求;我们的呼求也乐意包括‘盟约子民’(Popolo dell´alleanza)的子孙,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在人类宗教史上所扮演的角色”[14]。随后教宗呼求天主赐予“修好的恩典”以及“全人类和各国享有和平”,并以希伯来语祝福“和平(shalom)”而结束他的谢词。
当天上午教宗抵达纳匝肋,在那个时代当地的天主教信友人数相当多,他们以非常特殊的方式欢迎教宗的来到。教宗的车队行经那条——至今仍以“保禄六世”为名——大道,沿途搭设着缀满花卉的拱门,地面铺满具东方色彩的地毯,路边飘扬着教宗的旗帜。那真是人民和信仰的大节庆。教宗在仍在建筑中的圣殿的地下室奉献弥撒圣祭。
隔天,教宗到加利肋亚与耶稣和圣母玛利亚有关的地方朝圣参访。在返回耶路撒冷位于仍属约旦部分的宗座代表公署之前,教宗再度接受以色列总统迎接致意。当他向以色列总统致谢词时提到庇护十二世教宗并谴责某些方面对这位伟大教宗的怀疑和指控,他说:“就像我们一样,每位就近认识这位无辜灵魂的人士,无不体察这位教宗如何同情、怜悯人类的苦难,体会他内心的英勇和慈善。那些在战后含泪奔赴他面前,涕泣感激他救命之恩的人,都深知这位教宗的心怀”[15]。这席本来不在原稿上的话受到犹太人代表团非常冷漠的回应。某些分析人士认为,保禄六世这席话显示他勇敢维护历史真理和对他前人的记忆;另有些人则以为从政治与外交角度看,这席话不切时宜。
傍晚时分保禄六世回到宗座代表公署,接受了备受期待的东正教大公宗主教阿德纳格拉的拜访。在这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大公宗主教与罗马教宗互相拥抱并举行了第一次晤谈:这是两个教会在分裂十个世纪之后的创举。在这彼此友爱之举后,阿德纳格拉向保禄六世致词说:“我们真诚渴望近来双方所验证、并在这次受祝福的神形会晤中获得肯定的善意,能带来彼此的共融和更进一步地承行天主的圣意…。基督信仰的世界生活在分裂的黑夜中,基督信徒的眼睛疲于注视着黑暗。但愿这次相会成为获得祝福的晨曦”[16]。
次日,1月6日,保禄六世教宗圣地朝圣之行最后一天上午,他到阿德纳格拉宗主教在耶路撒冷的驻所回访这位东正教领袖。教宗致词说:“有关教义、礼仪和规律的分歧,将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以忠实尊重真理的权利、诚实评判问题、遵从爱德、忠于真理、在爱德中彼此体谅的精神,予以慎重思考。至于今后能够而且必须做的乃是:增强彼此的友爱,致力寻找新的途径,以过去经验的启发来推行爱德,随时准备宽恕,从对方身上辨识出善,而不是恶,一心只追寻神圣导师的芳踪”[17]。最后,教宗在阿拉伯兵团骑兵队的护送下,前往白冷朝圣,受到许多教友和守护圣地的方济各会士的欢迎。他在耶稣诞生圣殿地下室的马槽恭放了一尊耶稣圣婴态像并举行了弥撒圣祭。
毫无疑问,保禄六世教宗与东正教大公宗主教的会晤给他的圣地朝圣之旅平添了新意义。这件盛事的成果之一便是1964年秋季梵二大公会议第三阶段会议揭幕之初,大公东正教另又进一步派遣多位观察员与会,这是大公会议在开始之初早已恳切期待的。
1月6日傍晚保禄六世教宗回到罗马时,意外地受到罗马市民兴高采烈、凯旋式的欢迎。教宗在圣地时他们都守在电视机前跟随他每一项重要的朝圣活动。无数民众从罗马机场陪伴着教宗回到梵蒂冈。最后,保禄六世不得不出现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降福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群众。
- 参见G. Sale, «A cinquant’anni dal viaggio di Paolo VI in Terra Santa», in Civ. Catt. 2014 II 313-326. ↑
- 参见 G. Caprile, Il Concilio Vaticano II. Secondo periodo, vol. III, Roma, La Civiltà Cattolica, 1966, 438. ↑
- 同上。 ↑
- 同上,603。 ↑
- 同上,602。 ↑
- 参见J. Martin, «Les voyages de Paul VI», in Paul VI et la modernité dans l’Église, Roma,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84, 317-332; A. Melloni, L’altra Roma. Politica e S. Sede durante il Concilio Vaticano II (1959 – 1965), Bologna, il Mulino, 2000, 262. ↑
- 参见G. Alberigo (ed.), Storia del Concilio Vaticano II, vol. III, Lovanio – Bologna, Peeters – il Mulino, 1996, 528. ↑
- 参见U. Koltermann, «Paolo VI in Terra santa», in Il Regno-documenti 45 (2000/1) 67. ↑
- 参见A. Melloni, L’altra Roma…, cit., 263. ↑
- «Paolo VI pellegrino d’unione e di pace», in Civ. Catt. 1964 I 112. ↑
- 在教宗举行弥撒时突然停电,整个圣殿顿时陷入黑暗片刻,只靠几只烛光照亮着。之后,在两位礼仪人员陪伴下教宗低头进入小小的圣墓穴内,把罗马病患呈送给他的一支金质橄榄树枝放在坟墓上方的大理石板上并祈祷。 ↑
- L. Sapienza, Paolo VI in Terra Santa, Roma, VivereIn, 2014, 53 s. ↑
- G. Caprile, «Pellegrinaggio del Papa in Terra Santa», in Civ. Catt. 1964 I 183. ↑
- 同上,页184。 ↑
- 同上,页62。 ↑
- 同上。 ↑
- 同上,页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