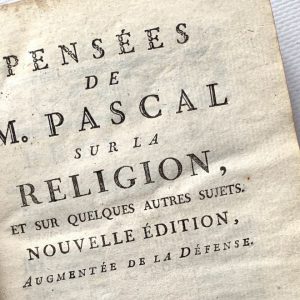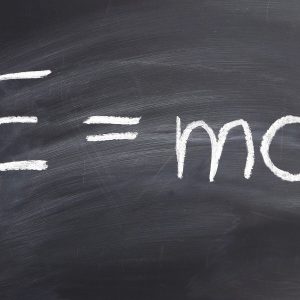基督徒应该倾向于以非暴力方式应对一切不公正,还是在某些情况下以武装反击作为一种合法手段来应对所遭受的严重迫害?近年来,这一问题在天主教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议的一方将非暴力视为对基督追隨者的要求,另一方则继续支持自圣奥斯定时代以来一直作为天主教传统核心的“正义战争”理念。于是,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神学问题由此而生。
这一争议的背后是对以非暴力抵制不公正的实际效果的质疑。非暴力行动是否能够确保其自身所寻求的和平与正义?是否可以在一切情况下奏效?还是说,遗憾的是,有时候必须诉诸武力才能有效地捍卫正义?事实上,以非暴力抵抗不公正的有效性并非这一争议的唯一关注点,而是涉及其他重要的神学和伦理问题。从《圣经》中,我们了解到避免使用暴力对于真正的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圣经》中“不可杀人”的诫命不仅是对所有基督徒的约束,事实上也是对所有人的约束,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这条诫命明确要求避免在可能通过非暴力行动实现促进正义的社会目标的情况下使用致命武力。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通过教导祂的追随者为和平奋斗而强调了避免暴力行动的重要性。耶稣在山中圣训中宣讲说:“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玛 5:9)。祂还进一步以这样的呼吁强调寻求和平的必要性:“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玛 5:44-45)。耶稣突出表明了基督徒非暴力生活方式的使命之深远,在放弃以任何威胁人类生命的胁迫形式来实现祂的目标的同时,祂甘愿承受,为传福音而献身,死在十字架上。
促进正义的基督宗教
在呼吁非暴力的同时,《圣经》也劝诫基督徒努力促进正义。《出谷记》是希伯来圣经的基础叙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面对以色列人在埃及人不公正的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天主眷顾了他们,希望将他们从不公正中解救出来。祂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梅瑟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号;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权势”(出 3:7-8)。然而,祂又补充说,为了伸张正义,这种解救的干预可能需要使用某些强制手段:“但是我知道,若不用强硬的手段,埃及王决不会让你们走。因此,我要伸手打击埃及”(出 3:19-20)。以色列先知们坚持不懈地为天主对正义的坚定承诺作证,与此同时,他们也再三呼吁人们要在团体生活和人际关系中践行正义。先知亚毛斯因此而宣称,在以色列,“但愿公道如水常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亚 5:24)。我们在《旧约》中所看到的以上见证不仅说明了正义对以色列人民的重要性,而且仍然是基督徒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基督徒对非暴力的承诺必须与对正义同样程度的郑重承诺相伴而行。
这些圣经经文是对天主教团体追求和平与正义的召叫的提示,人们显然不应以简单化或原教旨主义的方式来解读它们。天主的国度一旦完全实现,将使人类在这两方面的希望得到实现。因此,基督宗教伦理十分重视以非暴力方式追求和平,并同样认真的努力寻求公平和正义。在天主的国度里,当基督徒的希望在末世得以实现时,和平与正义都将完全实现。因此,基督普世君王节的礼仪宣称天主的王国是“真理与生命的王国,圣德与恩宠的王国,正义、仁爱与和平的王国”[1]。因此,基督的追随者受召促进正义与和平。
当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和平与正义的目标之间会存在张力。对基督徒来说,通过非暴力行动追求正义无疑是战胜虐待和压迫的必由之路,其中包括积极的非暴力抵抗。然而,人类的分裂有时会使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正义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人类罪恶的现实有时会导致人类社会在历史上无法实现天国所特有的正义、爱与和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被迫决定是否必须以放弃非暴力方式而使用致命武力作为优先选择才能制止各种欺辱行为。因此,当前争议所涉及的问题是:在基督宗教的非暴力承诺与为正义而努力的责任之间确认哪个目的更有说服力。在这个被人的罪恶所造成的冲突及不公正而扭曲的世界里,究竟是基督宗教对正义的承诺优先于对非暴力的承诺,还是对非暴力的承诺优先于对正义的承诺?这些问题已成为当今教会应以怎样的适当形式参与社会生活及国际事务的争议焦点。
告别“正义战争”传统?
一些天主教徒认为,应该在今天重新恢复教会历史中早期基督徒拒绝使用武力和参与军事活动这一做法的规范性价值。他们认为,始于后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徒参军既是一种统治者的拉拢,也是一种对福音的背叛,因此,非暴力才是基督徒的唯一正当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主教团体“基督和平会”(Pax Christi)于2016年在罗马主办的一场会议指出,必须以对非暴力的坚定承诺取代自圣奥斯定时代起即存在于天主教会中的正义战争传统。会议的最终文件指出:“现在已经是行动的时刻,我们的教会要成为鲜活的见证,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以促进积极的非暴力精神和实践,加强我们的天主教团体在采取有效非暴力做法方面的培育和练习。在这一切中,耶稣是我们的启迪和楷模”。
这一呼吁进一步指出:“我们相信不存在任何一种‘正义战争’。[…]此外,‘正义战争’可能存在的提法会阻挠对以非暴力为转化冲突之工具和能力的道义责任。我们需要一个与福音中的非暴力相一致的新框架”[2]。
这次会议以一些宗座及教会训导为基础。例如,若望二十三世在《和平于世》通谕中指出,核武器在当今的一些国家中扩散开来,其破坏力意味着“几乎无法想象在原子时代以战争作为维护正义的工具”[3]。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这一声明表示赞同,认为现代武器的危险是一个关于战争问题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危机。因此,大公会议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特征迫使教会“以全新的观念思考战争问题”[4]。此外,大公会议还将非暴力承诺确认为活出基督精神的行动,并对“那些不以暴力争取自身权利的人士”予以表扬[5]。
更近期的教会教义同样敦促天主教会在不断加强对非暴力承诺的同时远离正义战争传统。美国入侵伊拉克伊始,若望·保禄二世便立刻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他宣称,真正的和平途径“永远不会通过暴力,而总是通过对话。众所周知,暴力只会滋生暴力。那些来自冲突频发之地的人尤其清楚这一点”。他继续指出,战争“只能被视为一种失败的结果:它是理性和人性的失败。因此,但愿一种精神和文化冲击早日到来,以引导人们摒弃战争”[6]。
教宗方济各同样质疑战争在当代环境中的合法性, 并强烈主张致力于非暴力。他曾在不同场合中质疑正义战争的传统是否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他在其通谕《众位弟兄》中断言:“我们不能继续将战争视为解决方案,因为战争的风险很可能远高过其假设的效用。鉴于这一事实,今天很难依循多个世纪前提出的理性标准来谈论‘正义战争’的可能性”[7]。方济各在与莫斯科东正教牧首基里尔(Kirill)就乌克兰战争所进行的谈话中重申了这一立场,他表示说:“即使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也曾一度谈论圣战或正义战争。于今,我们已不能再以此为说辞”[8]。在以“非暴力:缔造和平的政治风格”为主题的2017年世界和平日致辞中,教宗强烈主张以非暴力途径面对国际环境中出现的问题。教宗表示:“愿非暴力成为我们的决定、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行动以及各种政治行为的特征”[9]。
从教会官方训导中所摘录的这些言辞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天主教当局正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致力于非暴力并因此而放弃一个在许多世纪中塑造而成的天主教关于战争与和平伦理观念的正义战争传统。
合法的自卫权
然而,天主教团体内外许多评论家却否认这种转变了的观念正处于发展中的事实。例如,天主教神学家马克·J·艾尔曼(Mark J. Allman)和托比亚斯·温赖特(Tobias Winright)认为,2016年“基督和平会”罗马会议的最终声明选择性地解读了圣经、天主教传统及教会的最新教导。同样,他们坚信,该呼吁未能充分关注那些必须通过武力才能有效保护人民免受严重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他们认为,该呼吁以错误的两分法将非暴力承诺与正义战争传统所阐释的事实相对立,而这一事实所指的是:使用武力是为了促进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和平,只有在用尽实现正义和平的其他手段之后,方可使用武力[10]。举例来说,这一呼吁忽视了圣奥斯定认为武力可以作为实现和平的手段这一事实。奥斯定指出,“即便那些发动战争者的残忍行为和人类所有的骚乱也都旨在实现和平”[11]。当然,对于这位希波圣人而言,战争的目的既可以是好的和平,也可以是坏的和平,既可以是公正的和平,也可以是不公正的和平;但是,他也同时指出,对战争进行道德和宗教评价而不承认冲突的目的之一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和平是错误的。艾尔曼和温赖特还指出,“基督和平会”所发表的声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梵二在赞扬非暴力的同时也假定非暴力行动的实施应“不损害他人及团体的权利与义务”[12]。此外,大公会议还明确指出,“一旦和平解决的所有可能性皆已用尽,便不得否认政府的自卫权”[13]。
作为一位正义战争传统方面的知名历史学家,詹姆斯·特纳·若望逊(James Turner Johnson)质疑“天主教会是否正在放弃正义战争的教义?”[14]。虽然若望逊并非天主教徒,但他出于对正义战争传统的学术研究而确信,天主教放弃这一传统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这样观察道:“某些不公正只能以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这种认识始终是正义战争观念的核心”。若望逊认为,正义战争传统并不构成难以逾越的困难,反而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对解决严重不公正问题作出贡献。因此,他在结合政治分析和历史研究的同时对天主教放弃关于战争在某些情况下道义正当的原则所提出的反对也便不足为奇。
道德的条件
那么,这个问题会涉及到哪些方面呢?尽管教宗方济各曾明确指出战争于今不再具备正当理由,但在其他一些言论中则表明他所采取的立场并非绝对。在“基督和平会”于2016年召开的会议上,教宗在致辞中指出,废除战争是与人类社会“最相称的终极目标”。但是,在同一篇致辞中,他也引用了梵二关于政府在竭尽全力以非暴力反抗不公正之后拥有合法自卫权的声明[15]。在2022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回程途中的那次重要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应该接受自卫武器时,方济各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如果在道义条件下完成,它可以是符合道义,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自卫不仅是合法的,也是热爱祖国的表现”[16]。教宗在此所谈的“道德条件”无疑是指正义战争的传统准则。事实上,在同一新闻发布会上,他建议“应更多地思考正义战争的概念”[17]。方济各似乎在说,对于如何理解正义战争传统所提出的合法使用武力的准则,以及如何应用这些准则,需要进行更认真的思考。
换言之,可以因此而认为教宗方济各是在敦促基督徒作出努力以非暴力方式战胜不公正的坚定承诺,而不是建议教会放弃有关正义战争的传统。非暴力承诺之所以重要,显然是因为不可杀人的诫命以及耶稣对基督徒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呼吁。
最近的政治事件表明,非暴力行动在抵制压迫和伸张正义方面相当有效。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和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列举了许多非暴力反抗不公正运动的成功范例。其中包括20世纪40年代末使印度赢得独立的甘地对英国殖民统治卓有成效的抵抗;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菲律宾“人民权力”运动;1991年爆发于波兰并导致苏联解体的斗争;以及南非于1994年取消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而成为多种族民主国家的事件[18]。事实上,最近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对于抵制不公正,非暴力往往比使用武力更有成效。政治学家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和埃里卡·切诺韦斯(Erica Chenoweth)通过提供大量实证表明,在反对专制政府不公正的国家运动中,非暴力运动往往比使用暴力手段的斗争更为成功[19]。这些证据表明,教宗方济各所提出的教会应采取一种以坚定的非暴力承诺为动力的伦理呼吁,对于追求正义而言,既不是天真,也不是政治上的不切实际。
与此同时,方济各显然并不是呼吁完全放弃关于正义战争的传统,而是恳请基督徒以至全人类要识别战争的巨大破坏性,而绝不轻易诉诸武力。他希望避免以倾向于使战争合法化的方式解释和利用正义战争的传统。参照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经典著作《正义与非正义战争》(Guerre giuste e ingiuste)这一书名,我们可以将这一传统描述为“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传统”,并以此解释那些在许多情况和理由之下诉诸武力的做法往往是非正义并应该避免的。事实上,鉴于教宗方济各所坚持的对于合法使用武力的道德准则的严格解释,当今的许多冲突,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冲突,都应被判定为不合法的。既然是不正当的,这些冲突根本就不应该被触发。然而,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方济各似乎并不反对在有必要保护无辜人民时使用武力。
真正的和平建设
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宗关于战争伦理的训导与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于1993年发表的声明《正义是以和平栽种的果实》(The Harvest of Justice is Sown in Peace)中所确认的内容相近,该声明是在他们此前的牧函《和平的挑战:天主的应许和我们的回应》(The Challenge of Peace: God’s Promise and Our Response)发布十周年之际发表的。1993年的声明重申,对冲突的道德评估应以承认“暴力带给人类和道德的可怕代价”为出发点。这一认识促使美国主教们强调,无论人的生命在何处受到威胁,捍卫人的生命都是“真正建设和平的出发点”[20]。这种对人类生命神圣性的认识,以及主教们对耶稣号召基督徒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强调,促使他们在基督宗教伦理的背景下对非暴力给与大力支持[21]。事实上,无论是美国主教们还是教宗方济各都同样建议那些渴望保护无辜者免受严重不公正待遇的基督徒以非暴力承诺作为他们的出发点。正如美国主教们所言:“在冲突局势中,我们的持久承诺应该是尽可能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正义。但是,当非暴力行动的持续尝试无法保护无辜者免受极端不公正待遇时,可以允许合法的政治当局使用有限的武力作为拯救无辜者并伸张正义的最后手段”[22]。
因此,美国主教们和教宗方济各都将非暴力视为基督宗教面对国际政治问题的核心。然而,在认识到冲突的根源是世界自身所具有的罪恶特性时,美国主教们也认为在严格限制下使用武力有时可能是必要的,但前提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出于正义的意图、使用适当的途径、具有成功的可能性且作为最后手段[23]。同样,我们也可以如此理解方济各对于战争的观点。只有当实现正义的非暴力手段已经用尽时,教宗才允许跨越“反对武力的前提”,以寻求为人类尊严和人权提供保护的和平。
最近,包括詹姆斯·特纳·若望逊(James Turner Johnson)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在目前的教宗及主教团训导中所达成的认同,即以非暴力方式为解决不公正问题之优先选择,实际上是对正义战争传统的放弃[24]。若望逊认为,天主教传统更倾向于一种包括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对正义的先决性维护,而不是一种推崇非暴力的假设。因此,在他看来,强调应尽可能通过非暴力方式寻求正义的假设应当被解读为对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传统的放弃。然而,我们则认为,若望逊的这一论点是错误的。圣多玛斯·阿奎那在解答“发动战争是否总是罪过”(拉丁语:utrum bellare semper sit peccatum)这一问题时,对有关和平与战争的伦理展开了论述[25]。之所以对战争是否总是罪过提出质疑,其原因毫无疑问是出于应在尽可能范围内避免战争的假设。事实上,若望逊本人也曾在1979年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此表示认同并在文章中指出,他将阿奎那最初对战争伦理的质疑(quaestiones)称为“正义战争的原始问题”,这些问题表明了“一个相当惊人的发现,那就是:关于正义战争,和平主义基督徒与非和平主义主张正义战争基督徒的共同点是一致的,即:对暴力怀有极度不信任”[26]。遗憾的是,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最近的著作中似乎忘记了自己早先关于非暴力与正义战争伦理之间密切关系的观点,尤其是在对最近的天主教辩论提出批评时更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可见,教宗方济各和美国主教团的观点涉及到应以一种互补关系来思考关于非暴力与正义战争的伦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福音和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敦促基督徒以非暴力的方式寻求正义便愈发显而易见。倘若无法通过非暴力方式有效地伸张正义,则应谨慎地执行正义战争准则。这意味着,倾向于支持非暴力有助于我们对正义战争准则的正确解释与执行。
首先,以非暴力方式应对不公正的前提加强了正当采取作为“最后手段”的正义战争准则的力度。只有在充分使用非暴力的举措之后,方可考虑使用武力。
其次,当 “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CISS)首次提出“保护的责任”理论时,对非暴力的支持。该委员会的“预防原则”强调,应使用外交及其他非军事手段保护人民免遭严重侵害,如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及战争罪行,等等。只有在外交努力显然无法保护人民免受这些严重罪行之害时,才应考虑使用武力[27]。
最后,对非暴力的承诺应加强冲突后的和平建设,包括努力通过重建甚至宽恕来实现和解[28]。从这一角度看,似乎更有必要从两方面继续深化并发挥非暴力手段的潜力:一方面是在促进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正如上文已经谈到的阿什-罗伯茨及斯蒂芬-切诺韦斯(Ash – Roberts e di Stephan – Chenoweth)通过相关研究而提出的实证观点;一方面是在冲突后为巩固和平这一“需要不断建设的大厦”(GS 78)的基础而进行重建的过程中。
可见,对非暴力的承诺可以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做出巨大贡献,因此不应被视为不切实际。非暴力前提的重要贡献明显地体现于教宗方济各为竭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中寻求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中。教宗多次呼吁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而努力结束冲突。这些呼吁表明,他坚定地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来寻求和平与正义以此来避免和克服暴力。这一承诺不仅体现于教宗敦促停火和外交谈判的声明中,也体现于他自愿为公正和平充当调解人的举动中。
因此,方济各同时体现了基督宗教对非暴力及正义战争传统的坚定承诺。在天主的国度里,完全的非暴力和圆满的公正都将会得到实现。然而,在历史存在的有限范围内,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将无法达到天国所应有的非暴力和正义。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将不得不就如何平衡非暴力与正义的价值做出明智的政治决定。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各国领导人能够追随教宗方济各,致力于对非暴力和正义的支持。这不仅将有助于他们在通过政治行动和外交手段寻求正义与和平的过程中理解非暴力的重要性,也将使他们看到非暴力与正义战争准则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非暴力伦理与正义伦理的互补性不仅可以从道义上指导各国领导人的未来行动,也将有助于塑造教会在公共生活中努力回应基督关于天国来临的承诺这一使命。
- 《罗马弥撒经书》,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序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普世君王。 ↑
- Pax Christi Internazionale, «Appello alla Chiesa Cattolica per promuovere la centralità della nonviolenza evangelica», 于2016年4月11-13日在罗马举行的《非暴力与公正的和平:促进天主教对非暴力的理解和承诺》会议结束时分发的文件(https://tinyurl.com/mr39ukus)。 ↑
- 若望二十三世,《和平于世》通谕(1963年4月11日),第67条。 ↑
-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简称GS),第80条。 ↑
- GS第78条。 ↑
- 若望·保禄二世,在以“宗教与文化:缔造新人文主义的勇气”为主题的第18届会议上致瓦尔特·卡斯珀枢机(Walter Kasper)的信函,2004年9月3日,4。 ↑
- 教宗方济各,《众位弟兄》(2020年10月3日),第258条。 ↑
- 同上,《与牧首基里尔的谈话》,2022年3月16日。 ↑
- 同上,《庆祝世界和平日致辞》,2017年1月,第1条。 ↑
- 参见M. J. Allman – T. Winright, «Protect Thy Neighbor», in Commonweal 143 (2016) 7-9 (www.commonwealmagazine.org/protect-thy-neighbor). ↑
- Agostino d’Ippona, s., La città di Dio, XIX, 12. ↑
- GS78. ↑
- GS79. ↑
- J. T. Johnson, «Is the Catholic Church About to Abandon Its Just War Teaching?» in Providence (providencemag.com/2016/04/catholic-church-abandon-just-war-teaching),2016年4月26日。 ↑
- 参见方济各,在“暴力与公正和平:促进天主教对非暴力的理解和承诺”会议上致彼得-K-A-特克森(Peter K. A Turkson)枢机的信函,罗马,2016年4月11-13日。 ↑
- 同上,访问哈萨克斯坦后在返回罗马时专机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2022年9月15日。 ↑
- 同上。 ↑
- 参见T. Garton Ash – A. Roberts,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参见M. J. Stephan – E. Chenoweth,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 (2008/1) 7-44; E. Chenoweth – M.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The Harvest of Justice is Sown in Peace, Washington, D.C., 1993, 3. ↑
- 参见同上,11。 ↑
- 同上,10。 ↑
- 参见同上,12。 ↑
- 参见J. T. Johnson, «Just War, as It Was and Is», in First Things (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05/01/just-war-as-it-was-and-is), gennaio 2005. ↑
- Thomas Aquinas, s., Summa Theologiae, II-II, q. 40, a. 1。斜体字为本文作者所标注。 ↑
- J. T. Johnson, «On Keeping Faith: The Use of History for Religious Ethics», in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7 (1979/1) 113. ↑
- 参见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ttawa, Canada, 2001, nn. 4.32-4.43 (https://tinyurl.com/27uy87m2). ↑
- 参见D. Christiansen, «Just Wa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nviolence, Post Bellum Justice, and R2P», in Expositions 12 (2018/1) 33-59 (expositions.journals.villanova.edu/article/view/2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