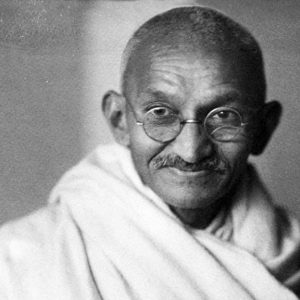就像相识已久的邻里,我们诧然发觉Facebook已有20年的历史。之所以令人叹奇,是因为这一事实历时虽短,却仿佛早已与我们为伴。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并随着此后20年中的迅速发展从最初面向美国大学生的服务一跃成为一个为全世界提供服务的工具。然而,有些人却对为何庆祝其成立20周年纪念之问题感到不可思议。
Facebook是什么?它既是一家公司,又是一种产品。作为前者,这个广为人知的公司是学术、新闻报道以至一部影片的焦点[1]。继赢得较高股票市场份额之后,它拓发了新的领域,并更名为“Meta”。就其产品而言,虽然它本身已广为人知并被广泛使用,但事实上却并未得到人们的理解:“对于全世界数字惊人的用户而言,Facebook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他们几乎从不会停下来琢磨一下它的作用”[2]。据管理者之一安德鲁·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称,Facebook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将人们联系起来’[3],而且在这方面卓有成效。与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不同的是,为了建立这种联系,Facebook要求用户显示自己的真实姓名:这也是它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于用户而言,Facebook上的联系如同他们的日常身份一样自然。
本文将针对作为传播手段的Facebook(作为产品)进行分析,尝试以传统传播范式来把握其本质,通过其意想不到的后果来理解其运作,并最终就Facebook在媒体世界所造成的变化提出一些反思。
一个传播机构
Facebook是什么?这并非一个单单出于熟知它便能搞懂的问题:需要理解某一沟通方式的本质。作为一种沟通方式,Facebook虽新颖却并不稀奇。它并非第一个社交网络,社交网络也并不是互联网的产物。自古以来,人们始终如一地致力于结交朋友并了解他们的生活、共商大计、念叨熟人熟事、赶时髦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同样可以在Facebook上进行。尽管公司的叙事立即承认说Facebook的许多基本理念均来自原始数据,但作为一个工具,Facebook不仅能够更好地融汇各种事物,而且还能更迅捷地满足用户需求[4]。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四大定律应用到Facebook案例中,我们不仅会对其定位拥有更清晰的思路,而且还能更好地理解它的影响[5]。这位加拿大学者认为,每一种新媒体都会改进、逆转、恢复或淘汰以往的传播形式。这一点对Facebook的适用程度不亚于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Facebook改善了社交联系,其中包括个人联系及我们对联系的理解,因为它为建立社交联系扩展了规模、提高了速度、补充了新的联系方式以及新话题。但这种规模也在减缓这一进程的同时使其发生了逆转,因为它导致人们既无法了解数十亿其他用户的信息,也无法跟踪他们的动向;此外,它还在人们最私密的联系之中纳入了此前素不相识的个人乃至公司。脸书恢复了以往媒体中的一些功能,包括归属于一个社群[6]、接收新闻、写信、了解销售情况,加入粉丝圈(fandom,这是一个新名词,指因同一喜好而组成的社群)、分享媒体以及张贴博客[7]等等。最后,它使某些传统媒体形式被淘汰,其中包括邮递、面对面接触、报纸等等。
如果说Facebook(产品)与其他媒体具有如上所述之关系,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在冥思苦想了这个问题之后,泰娜·布彻(Taina Bucher)终于不再纠结,投笔写道:“Facebook 就是 Facebook”[8]。此话言之有理,因为Facebook在这20年中不断发展和更新自己,不仅吸引了其他媒体,也扩展了它连接人的使命。它不断进行调整,利用从用户那里收集到的大量数据为他们提供自己认为更好的体验[9]。
按时间顺序排列的Facebook大事记[10]记录了该公司在成立二十年时间中对其产品做出的更新:其中有许多对于用户而言显得平易近人,甚至几乎具有决定性,以至有人可能会纳闷该公司如何在不做此类更新的情况下得以生存。Facebook在2004年诞生时不过是一个网站而已。只有在苹果公司推出iPhone八年后的2011-2013年,它才增设了功能,成为一款手机应用程序。粗略按照时间顺序回顾,Facebook的发展伴随着增设以下功能,即:姓名和联系方式、照片、照片标签、动态消息(用户可以发布供他人查看内容的landing page,用户可以进而找到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好友间相互联系的社交图谱;Facebook的Note(简短信息,属于博客活动);News Feed(信息更新,Facebook的一份关于好友的信息排序以及通过算法筛选出的被其视为用户感兴趣的资料);Facebook Platform(脸书平台,它专属于开发人员,使他们能够在Facebook界面创建应用程序,比如网页链接;Facebook Beacons(即脸书信标,一种广告系统);Facebook Credits(脸书信用点数,可用于金融交易和支付);Like(“点赞” )按钮,可在状态更新和评论中标记好友;Community Page(群组页面,群外人信息流页面);Open Graph(用户所认识的人的兴趣图谱);Facebook mobile(手机应用程序)、视频聊天、Facebook Timeline、Facebook Exchange(一种广告竞价系统)、表情符号、DeepFace(用于识别照片中人脸的面部识别系统)、Newswire(Facebook的即时通讯工具)、内容管理和Facebook Live。此外,Facebook还收购了Instagram、WhatsApp、Oculus VR等公司,它们为数据分析、存储等提供组织结构性支持。作为一款产品,Facebook从多个方面将人们及其兴趣联系在一起。使用Facebook的用户意味着被连接起来,对于许多人而言,Facebook就是互联网。作为一家公司,Facebook积极捍卫在连接人们的方式上的霸权地位,并收购竞争对手或其员工,以保持本公司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了解Facebook是一个挑战,因为它已随着不断的更新而变得面目全非。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所有上述特征,布彻等人作出了一系列比喻,即:Facebook是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公共空间,一个城镇广场和客厅,一种开放式互联网的实现,一个社群,一个公共传播组织,一个电话簿,一个新闻来源,一个邮局,一种服务,一个平台,等等[11]。Facebook是一个媒体环境,一个各种实践和各种通信设备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连接设备。上述比喻提醒我们,Facebook已尽可能灵活地为尽可能多的用户提供了服务,因为它不仅只是一种产品,而且还是一家需要扩大用户和发展壮大的公司。为此,其用户数量从2004年的7万增长到了2016年的18亿[12]。
了解Facebook:使用与满足的类别
我们可以采取另一途径,通过以传统传播模式研究Facebook而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了解。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13],使用与满足理论这一始终以某种形式用于传播研究的方式所探讨的论点是,人们使用媒体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在此基础之上,传播学者针对人们为什么使用每一种新媒体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了许多原因,并试图将这些原因归结为几个主要类别。在这些原因中,典型的需求包括搜索普遍性信息、决策效用(也就是在投票、购买产品或采取决定时寻求帮助)、娱乐、人际效用和准社会互动(接触或追随演员、人物以至虚构人物)。
这些类别无疑同样适用于Facebook,并使人们了解其重要性。用户通过Facebook而达到诸多目的、满足各种需求。作为一个开放平台,它为用户和内容提供商提供了实现多种沟通的绝佳机会,其中首屈一指的是信息搜索,人们籍此而分享个人信息、与家人及朋友保持联系、查询其他人的位置信息、与旧时的同学及同事重新取得联系、保持社交联系。这种信息搜索具有一种监控作用,因为用户可同时监控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其中的个人。Facebook也是一种信息资源,不仅涉及朋友和公司,还涉及地方、国家及国际事务:对于许多人而言,它是最新消息的首要来源。与通常的使用与满足类别不同的是,Facebook上的信息搜索与人际效用类别相重叠,因为人们所搜索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与他人有关的:八卦是信息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际效用并不仅限于此。Facebook是一个用以组织团体及活动的媒介;它提供信息,并与商业、宗教、教育或娱乐团体建立联系。在此,这些类别同样是相互重叠的,因为Facebook为准社会互动提供大量资源。人们无需认识自己的Facebook好友:实际上,对名人生活的关注似乎给许多人带来了满足感。
如前所述,决策功能同样在Facebook的使用中发挥了作用。人们通过Facebook提高对各种问题的认识;公司将其作为营销和销售平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Facebook上开设网页,引导人们在医疗健康、娱乐、科学及其他各种服务方面做出抉择。政治团体利用Facebook教育、说服甚至欺骗选民。人们在几乎涉及所有问题的支持小组中寻求指导。Facebook提供有关医疗健康、科学、宗教、政治等方面的非正式信息来源,其目的是在指导人们的决策的同时充当新闻实验室(newsletter)。
最后,人们以Facebook为乐。即使这一类满足也与其他类型的满足相重叠,因为人际交往中的娱乐通过观察他人的生活而得以实现。不过,Facebook也是一个游戏平台;它不仅是粉丝的集合地,也是自我表达的方式和消磨时光的方法。
简而言之,就传播研究中应用的使用与满足类别而言,Facebook似乎是一种非传统媒介。就传统媒介而言,以往的研究很容易识别和区分人们对电视的使用,而Facebook则使人们的使用动机变得更加难以分辨。这种看法似乎也很现实,因为Facebook似乎提供了人们所期盼的一切,尽管人们的动机难以被明确界定。
意外后果
这些重叠性使用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作为一种普通沟通工具,Facebook可能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有意和无意的后果并不足为奇。由于用户及功能如此众多,在参与动机以及对其准则的解读方面出现一些混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更加多样化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群体来说,那些原本仅限于将本校学生联系在一起的相对单一的大学生群体的做法并不奏效。此外,必须指出的是,Facebook(公司)最初对用户的态度相当温和,低估了种种不当行为。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指出,Facebook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整个公司历史上始终信赖他人,并没有努力防止不当行为。因此,多年来,Facebook的功能既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招致与日俱增的批评。
例如,作为产品,Facebook起初是朋友间共享的论坛;而作为公司,它主张言论自由[14]。这一直接目标,与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初衷,既实现了人们所期望的言论自由,也导致了虚假信息、欺凌、仇恨言论、骚扰、不当照片和不良行为的意外增长。 “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分享内容的问题也日益增多” [15]。早在2005年,该公司就开始制定内容指南。两年内,美国各州政府开始向Facebook施压,要求其监控内容并删除色情内容,尤其是对儿童构成威胁的内容。由于Facebook的开放注册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访问,一些不赞同美国言论自由观点的政府就其国内被禁内容(通常是政治性的)发表了意见。有关不当内容的问题依然存在。
另一个例子是,该公司因改善用户体验而收集了海量数据并着重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使其能够在“新闻提要”(News Feed)中推出建议内容,包括朋友的帖子及广告。公司自成立之初就开始收集用户数据,其中大部分是按照例行程序进行。后来的功能,特别是“点赞”按钮(即使在服务之外的网页上也同样鼓励用户点击此按钮表示赞同),使Facebook(公司)能够收集其用户的联系数据,包括他们在Facebook上的朋友,也包括那些并非该平台客户的朋友[16]。
实际上,该公司的整个生产模式不是建立在创造内容上,而是建立在允许甚至要求用户创造内容上。这种对用户分享信息的鼓励导致了对数据隐私的开放态度。收集到的数据使该公司能够对其用户进行分析,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因为这些分析利于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
另一个间接效应证明,以广告为目的的数据收集成为一个始料未及领域中的宝贵商品,这个领域就是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运动。由于致力于自由表达,Facebook通常对政治广告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即使这种广告涉及虚假信息;该公司为政治言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7]。由于鼓励信息共享,Facebook(产品)成为政治信息的重要来源,公司认为不应对此进行干涉。
布彻认为,如上所述使得Facebook在政治上扮演了几个重要却间接的角色。首先,“由于Facebook在选举及政党方针政策中的作用,它已成为选举以及[……鉴于其潜在用途]影响选民行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次,“Facebook被用于组织政治抗议、发起社会运动或引导政治活动”。第三,“Facebook被当作一台造谣机,或[……]被专制政权用以限制抗议活动、控制民众,甚或导致暴行”。第四,“Facebook 受法律监管,[……]就其本身而言,它通过自己的政策及标准而规范如何使用” [18]。虽然该公司并无意成为政治工具,但这已是木已成舟。
只有当Facebook涉及隐私和政治时,另一种间接效应的程度才会显现出来。2015年12月,《卫报》展示了“克鲁兹(Cruz,美国政客)如何在竞选活动中盗用了Facebook资料” [19]。尽管内容制作和处理的合作伙伴如何掌握数据并对其进行操作的细节有些错综复杂,但大多数人当即便觉察到了隐私保护的缺失。脸书(公司)改变了对隐私的态度,因为它在最初的模式中假定人们希望自己的信息被公开:无论是喜好、关系状态,还是点赞;只是到了后来,该产品才允许人们刻意选择对某些信息的保护。然而,这些选择既未对个人形象也并没有对基于这一因素的个性总结产生根本影响:大多数用户想当然地高估了实际存在的隐私保护,并因此而未能预见或理解他们的个人信息可能会使他们受到怎样的劝说和操纵。对此该公司虽了如指掌,至少是在广告领域,但在保护用户信息方面却采取了最低限度的措施。
另外,其他隐私风险也出现在Facebook的核心部分。信息透明构成了该企业潜在的危险成分。脸书(产品)鼓励开放共享及诸如“新闻提要”(News Feed)或“开放图谱”(Open Graph)等某些有助于用户与自己的朋友取得联系并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的功能。这些辅助服务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八卦、从他人活动中取乐、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了解最新信息,甚至对自身环境进行某种监视的愿望。一方面,这似乎是保持联系的好方法,反映了公司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意图;另一方面,与他人取得联系的能力使得跟踪骚扰(stalking)及其他不当行为成为可能。[20]事实上,当 Facebook(公司)推出“新闻提要”(News Feed)时,用户就将该产品改名为“跟踪骚扰者的书”(Stalker-book)。
最后一个间接效应的例子与该公司宣称的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愿望有关:这导致Facebook的用户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然而,反过来,这种国际扩张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暴露出该公司缺乏跨文化知识与理解,例如,这导致了缅甸的悲剧,新的互联网和Facebook用户随即将那些煽动迫害少数民族的帖子信以为真[21]。
几乎Facebook的所有创意最终均会带来解决一些不必要问题的需要,这些创意包括帮助人们建立联系、在新闻推送中加入朋友的信息、监控他们的活动、推荐产品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Facebook为快速尝试新创意而依据其非正式座右铭“快速行动,打破常规” [22]行事的结果。这些不期而然的后果不仅归咎于企业的短视,也基于一种其潜力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新媒体。
不断演变的媒体世界
Facebook是通信变革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通信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在扩大其规模、加快其速度、丰富其方式的同时加强社交联系。在过去二十年里,Facebook较快地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它帮助发明并推广了一种新的交友及社交方式。
人们不需要成为末日预言家,也能从这一新的通信系统所带来的种种负面社会影响中窥出部分真相。关于Facebook的许多学术论文皆聚焦于这种强大社交网络所带来的影响上。Jamal Sanad Al Suwaidi 列举了其中的一些负面与正面影响,但他承认,这些影响是所有社交网络而不仅仅是独属于Facebook的特点:随着社会注意力向网络转移而造成的非数字社交联系的瓦解以及家庭纽带的丧失;通过与各种不同思想的接触而产生的社会价值观变化;文化转型;孤独感;依赖数字世界来满足情感需求;虚拟社区的发展;认知不平等和对教育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新的商业模式;跨国贸易的增加以及对不同群体的开放[23]。那么,如何解释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呢?
Facebook在社会范围内的迅速发展有助于解释其相互矛盾的影响。出于拥有众多社会关系并且耳闻目睹素昧平生者之间联系的可能,其结果是导致了互动中的去语境化或语境混乱。从传统上而言,作为人际交往指导的社会准则、行为规范是经过多年发展并且在各自社会群体的基础上约定俗成的。然而,Facebook的运作规模则削弱了通过直接接触而形成的行为控制。
同样,脱离语境会使人们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更趋向于欺凌,也更容易受到欺凌,他们在表达对外国人的仇恨言论时更加无所顾忌,更愿意相信种种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以至阴谋论,也更难以在大量未经过滤的信息所带来的心理健康挑战中找到平衡。
与此同时,社会规模的变化也引致隐私的丧失。总的来说,组成家庭及私密社群的成员都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一部分隐私:人们会自嘲地公认说小城镇中缺少隐私。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自己会如此公开地向那么多人提供如此多关于自己的信息,更不用说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剥夺我们通常寄托在心理防线、自尊甚至行为理由上的安全感。
在这些领域,通过这些方式,Facebook(产品和公司)间接地重新定义了人类友谊及其构型,甚至可能重新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它让自己版本的人类友谊变得简单,同时为每个人发送和接收更新,并创立了罗伯托·西曼诺夫斯基(Roberto Simanowski)所称的“情感计算产业” [24]。这是因为 Facebook(产品)重新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交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个人的物理位置并不重要,因为比社交空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虚拟世界。他们的虚拟时间也是如此。脸书不断提醒用户查看好友的动态,或花时间玩与好友相同的游戏,甚至建议如何打发时间[25]。如是,Facebook定义了用户的生活参数。
无法将Facebook清晰地映射到传播的用途和令人满足的模式中,这说明了它与其他媒体的不同之处。Facebook做着其他媒体所做的一切,但有一个根本区别:与广播、电视和电影相比,它是一种更具亲和力的媒体。事实上,无论广播、电视和电影在叙事、声音或图像方面多么令人身临其境,它们都在用户和内容之间设置了一个可识别的媒介。另一方面,由于Facebook依赖于私密关系,用户很容易混淆沟通的动机:信息搜索变成了一种寄生社交关系;监视变成了跟踪;人际实用变成了娱乐;甚至友谊也带有寄生社会的性质,因为该平台无形地介入了人们的生活。这些重叠的使用和满足使 Facebook(产品)作为一种媒介更难理解和解释。不过,其常见但被迫的亲密关系和重叠使用可能有助于解释该平台的一些意外后果。连接用户的算法放大了一切,进一步模糊了在面对面环境中形成的界限和社交规则。面对如此多的可变性,应如何预估其后果呢?
同时,Facebook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也促生了这些变化。西曼诺夫斯基对此做出如下总结:“通过邀请人们体验一种反思性贫乏的自我体验,它产生了不再对这一过程感到沮丧的主体。这就将它置于肯定性社会关系的趋势之中,同时它又促进了这种社会关系。Facebook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它让我们有可能爱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 [26]。
那么,Facebook 是什么呢?我们想再用一个比喻来回答:Facebook(这一产品)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自己,照出了我们的复杂、惊奇以至罪恶。
- 参见T. Bucher, Facebook, Cambridge, UK, Polity, 2021; D. Kirkpatrick, The Facebook Effect: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mpany That Is Connecting the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R. Krasnow, «In Your Feed: Books About Facebook’s History & Influence», in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www.nypl.org/blog/2021/02/04/facebook-booklist), 2021年2月4日;S. Levy, Facebook: The Inside Story, New York, Blue Rider Press, 2020年。此外,Bucher列举了400余份科学出版物作为参考文献,而Levy的论述则更倾向于新闻性质,其文献引用目录篇幅为30页。 ↑
- T. Bucher, Facebook, cit., 75. ↑
- S. Levy, Facebook…, cit., 441. ↑
- 参见同上,第7-13章。 ↑
- 参见M. McLuhan – E. McLuhan, La legge dei media. La nuova scienza, Roma, Edizioni Lavoro, 1994. ↑
- «Un’entità sociale, economica e politica che comprende famiglie legate da parentela» (J. S. Al Suwaidi, From Tribe to Facebook: The Transformational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Abu Dhabi,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2013, 12). ↑
- 参见同上,22 f. ↑
- T.Bucher, Facebook, cit. ↑
- 参见S. Levy,Facebook……,同前,第16章。 ↑
- 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 (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Facebook);S. Levy,Facebook…,前引,第7-13章。 ↑
- 参见T. Bucher,Facebook,同前,35;51 f。 ↑
- 参见维基百科,引用如前。 ↑
- 参见P. Palmgreen – L. A. Wenner – J. D. Rayburn, «Relations Between Gratifications Sought and Obtained: A Study of Television New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7 (1980/2) 161-192. ↑
- 参见S. Levy, Facebook…, cit., 111; 246 ss. ↑
- 同上,第246页。 ↑
- 参见同上,205 s. ↑
- 参见T. Bucher,Facebook,同前,第161页。 ↑
- 同上,第165页。 ↑
- S. Levy, Facebook…,前引,418。 ↑
- 参见 T. Bucher,Facebook,同前,第 108 页。 ↑
- 参见同上,188-194。 ↑
- S.Levy, Facebook..., cit., 6. ↑
- 参见 J. S. Al Suwaidi,《从部落到 Facebook……》,引用如前,第 66-74 页。 ↑
- 参见 R. Simanowski,Facebook Society: Losing Ourselves in Sharing Ourselv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XVIII. ↑
- 参见 S. Levy,Facebook……,前引,165。 ↑
- R.Simanowski, Facebook Society…, cit., XIV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