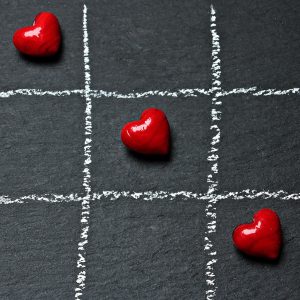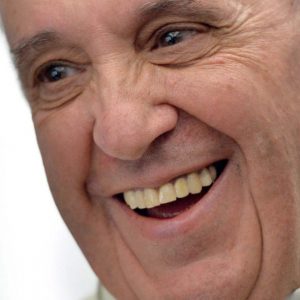文学能否滋养并支持基督徒的生文学能否滋养并维支持基督徒的生命?这一问题涉及教宗方济各发表于2024年8月4日的信函——《文学在培育中的作用》(简称RLF)[1]的核心思想。我们会在阅读这封信函时发现,这个答案不仅是面向司铎及牧灵工作者,也是写给所有基督徒。于此,本篇短文将在简要介绍其内容的同时强调指出为我们而言尤为重要的段落。
若想选择一个出发点,一个能抓住这篇短小但内容丰富的文章中的相关建议的“座右铭”,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地指出,文学是一段个人的、富有成果的心灵之旅,因为它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 “为心灵开辟新的空间”(RLF 2)。文学是一片憩息和慰藉之地,“让我们远离对我们不利的其他选择”(同上),它不仅在孤独的时刻与我们为伴,而且也在沮丧的时刻陪伴着我们:疲惫、愤怒、失望是动荡的情绪之海,一本好书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情绪。
阅读是一种积极的姿态
教宗提示道,阅读不同于那种滋生于某种偏见的思想,它绝非一种被动的姿态。读者与作品相遇并对话,双方互通有无,给予对方各自所有。阅读对于圣依纳爵·罗耀拉而言是一个爱的“形象”,也就是各自之所为然以及各自之所有的交流。事实上,无论是一段小说还是一首诗歌,都并非一个完整无缺、自成一体、无需进一步润色的整体,而是一个“呼吁”合作且易于实现的事实。读者将作品与自己的想象力、能力和愿望“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反向来看,读者的个人经历千差万别、各具千秋,它们是由作家照亮的经验宝库。
方济各积极提倡将文学作为神学院司铎培育过程的组成部分。与神学和哲学相比,文学既不是一种“可容忍的”娱乐形式,也不是一种“次要的”文化体验,它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价值:是“通向人类文化核心,更具体地说,是通向人的心灵”的一扇大门(RLF 4)。教宗的意志格外坚定,他指出:“通过这篇文章,我希望提出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即文学必须在圣职候选人的培育过程中得到高度重视”(RLF 5)。
人类对生存的强大渴望是文学的生命之本。教宗写道,他在阿根廷圣达菲(Santa Fe)神学院高中任教期间学到了这一点,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耶稣会修士,他应邀为中学高年级学生讲授文学。通过增强学生对当代文学的好奇心,他成功地激发了他们对历史名著的兴趣。这里涉及一个“渴望”与研究的问题。对此,他感叹道:“最终,心灵不停地继续探索,每个人都会在文学阅读中找到各自的道路”(RLF 7)。因此,文学探索可谓个人自由的空间。教宗对这一不可磨灭的心理和精神因素深信不疑,他在信中写道:“例如,我喜欢悲剧艺术家[…]当然,我并不是在要求你们阅读我所读的文集。每个人都 能找到与其个人生活有关的书,并将它们当作真正的同行伴侣。没有什么事比强迫自己付出巨大努力去阅读那些莫非是别人心目中的必读作品更弄巧成拙的了”(同上)。
对于教宗方济各而言,经常阅读文学作品是与当代文化进行对话不可或缺的一座桥梁,对此,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亦早已予以肯定。宗座信函在引用相关段落时指出:“文学和艺术[…]的追求是抒发人的固有特性”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最崇高还是最卑微的时刻,都可以成为讲故事和写诗的素材。教宗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是珠宝盒,是宝库,是历代男女的象征、信息、激情和恐惧的守护者,倘若我们忽视文学,我们怎么可能了解新的和古老的文化核心呢?(参见 RLF 9)。在历史上,教会曾多次与其同时代的文学和哲学文化对照。
该信函引用了凯撒勒雅的巴西略(Basilio di Cesarea)以及《宗徒大事录》中所记载的圣保禄在阿勒约帕哥(Aeropagus)的著名且重要的讲道,在讲道中,为了得到雅典人的理解,宗徒保禄将埃皮门尼得斯(Epimenides)与索利的阿拉图斯(Aratus of Soli)这两位诗人的诗句如此结合在了一起:“ 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说的:「˩[2]”。因此,不仅是牧者,事实上每一个希望与时代对话的信徒都必须像保禄撒种者(spermalogos)那样,而不是如同“侃侃而谈者”,正像这个词的词源所表明的,“撒种者”,那是指圣神“在事件、感性、欲望以及心灵深处的张力及社会、文化和灵性背景中”(RLF 12)播下了的种子。
阅读可以训练听力及对话技巧
此外,教宗方济各也在这封信中指出了阅读的其他积极作用。经常阅读的人可以扩大词汇量,提高叙述能力,这种能力也可以被理解为自我表达能力。这是一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涌动。另外,阅读还能让人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情境,促使我们做出判断,从而使其自身成为辨别和选择的学校。教宗引用克莱夫·斯塔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的话指出:“通过阅读文学巨著,我可以在化身为千千万万个人物的同时始终保持真我”(RLF 18)。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则写道,小说“可以在短短一个钟头里向我们滔滔不绝地道出所有可能的悲欢离合,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则需要花费多年的时光才能了解到其中的凤毛麟角,而且其中最强烈的部分往往从不会向我们显现,因为它们产生的速度太慢,使我们难以觉察”(同上)。教宗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一起强调了培养聆听能力的宝贵之处,即:聆听能治愈心灵的自我封闭和“灵性失聪”。最重要的是,文学能让心灵保持活力和温情,保持其被感动的能力。面对天主的奥秘、造物之美妙和人类的多样性,缺乏情感能力的心灵怎会有为之而惊叹的体验呢?
司铎与诗人之间的相似之处
教宗方济各与卡尔·拉纳(Karl Rahner)一样,谈到司铎与诗人之间的相似之处[3],因为二者同是“向无限敞开”、“唤起不可言喻,趋向不可言喻”(RLF 24)的文字工匠。在拉纳看来,“富有诗意的话语因此而唤起天主圣言”(同上)。如果说天主圣言及耶稣基督的本体实际上就是天主,那么所有与之相类比的人类语言皆含带着固有的怀旧迹痕,为世世代代的男男女女蕴藏于心。
教宗坚信阅读对读者所具有的激活力,于阅读而言,读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通过阅读小说或诗歌作品,读者“阅读”作品,也“被作品阅读”,作品本身之所以是基督宗教的,不是因为它“具有启发性”,而是因为它赋予内在的辨别力以生命,而内在的辨别力是灵性生活中最重要的行为之一,有助于确定一个人在时间和世界中的方向[4]。
令人回味的是,教宗用“望远镜”这一形象来表达文学在聚焦经验方面的“更多”:“望远镜”是一种用来观测远方的工具。就像望远镜一样,小说和诗歌使我们将简单的日常经验与更广阔的人类现实联系在一起。阅读,“简而言之,就是帮助我们高效体验生活”(RLF 30)。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确存在着一种风险:那就是持有一种回避复杂性的“简化”视野。一味追求高效、多产、得当可能会使生长繁殖能力下降。方济各引用福音书中种子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正如耶稣在播种者的比喻中所提醒的那样,种子需要落在深土里,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出累累硕果,而不会因缺乏根基或被撒在荆棘中被窒息(玛 13:18-23)”(RLF 31)。唯有阅读中的舒缓和无偿,才能捍卫聆听和沉思的时间和空间。教宗方济各在其中最有启发性的一段话中写道:“就这样,文学成了一个操练场,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和探索神秘人物与情境的真相,因为这些人物和情境充满了无数的意蕴,而这些意蕴只能部分地体现在类别、解释方案以及因果与手段-目的的线性动态中”(RLF 32)。此外,教宗还在重申使人联想到隐修院传统圣言诵祷(lectio divina)的沉思消化ruminatio滋养这一形象的同时提出了另一个形象:吸收,也就是说,将文学作为摄取生活及其意义的一种方式。
救赎的同理心与神贫
在结尾处,教宗总结了信中各种看法及建议的主导思想。文学在增进对他人生活的同理心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能力和基本作用;文学是“认同他人观点、状况并感受他们的能力的基本载体,离开这种能力,既没有团结,也没有分享”(RLF 34)。正如刘易斯(C. S. Lewis)所言,阅读就是“通过他人的眼睛看问题”(同上):通过了解他人的脆弱,我们可以更好地自我反省。文学作品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人类丰富而悲惨的经历,让读者“学会缓慢地理解,学会谦逊地拒绝简单化,学会温顺地不通过评判而控制现实和人类的状况”(RLF 39)。方济各重申了他在其他场合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当然需要评判,但决不能不顾忌其有限范围:事实上,评判决不能沦为将其打入死牢、一笔勾销,或是因被无情的法律至上一叶障目而压制人性”(同上)。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使人得到救赎的贫穷,这是一种福音理解中的神贫,它帮助读者避免以自我为中心,把握界限感,并训练他们“放弃对认知性及批判性经验的推崇,教给他们一种神贫,而这种神贫是异常丰富的源泉”(RLF 40)。
在这封书信的最后几个段落中,方济各再度向司铎及神学生着重申明了文学的培育作用,他指出,文学“使人自由而谦卑地行使理性,获取对人类语言多元性大有脾益的认知,提升自己对人性的敏感度,并最终敞开灵性之门,通过多种声音聆听天主之言”(RLF 41),因为司铎与诗人之间神秘的相似性体现在神言与人言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中,这就是“圣职”,是聆听与同理心的服务。
- 参见教宗方济各,Lettera sul ruolo della letteratura nella formazione,Città del Vaticano,2024年7月17日。 ↑
- 宗 17:28 ↑
- 参见A. Monda, “La ferialità della vita nei versi dei poeti”, in L’Osservatore Romano, 8 August 2024, 4. ↑
- 参见A. Spadaro, «L’arte di scovare la fede nei libri», in il Fatto Quotidiano, 14 agosto 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