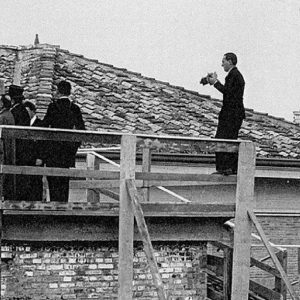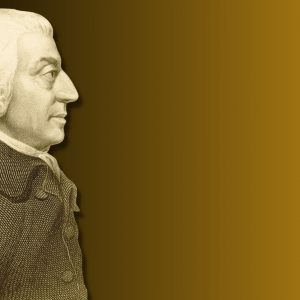重思一个永恒的主题
人们普遍认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更不要说精神病学),其主要关注范畴是人类行为中“病态”的一面:这些学科通过对各种症状及可能后果的解读而探索有效的治疗方式。这一途径无疑至关重要,对人们的生活亦有所帮助,但当它被绝对化的时候,则有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导致以偏于低沉以至最黑暗的单一色调看待现实之类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生存中的一些决定性主题,例如希望和感恩,虽然能够为应对困境提供重大帮助,但实际上却恰恰因为其“健康”因素而在心理学研究中拥有较小空间[1]。
由此而传递出的关于世界和人类的景象并不是最令人欣慰的,而且会在推导出相应逻辑结论时引起不少困惑。在一次以利他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上,时任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的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在致开幕词时坦言倾向于以过于阴郁和狭隘的滤镜看待人类,这不仅使人们难以认识到自身可能存在的“良善”,而且会最终阻碍任何相反的尝试:“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不仅对受私心驱动的人进行描述,而且还或明或暗地教人必须如此”[2]。持同一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的立陶宛裔犹太精神病学家欧文·亚洛姆(Irvin Yalom),他在一部精神分析式自传《妈妈和生命的意义》(Momma and the meaning of life)中指出了研究全面的、关于智慧的问题的困难,尽管这些问题对于治疗工作而言不可或缺:“精神病学著述除了将‘好’人格定义为一种对莫名的冲动的抗拒,很少对其特征进行探讨”[3]。正因如此,关于诸如无偿性、同理心及利他主义等“麻烦”主题的调查研究相对贫乏。
尽管如此,不乏存在着相反的反应。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否定将心理学变为对病态的分析、治疗且同时只关注有问题的人或有发展缺陷的人的倾向。对于这种对人的“病态”解读,他反驳说,在研究对自身及个人生活感到满意的主体时,可以发现人的心理动力之新且重要的要素,从而恢复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意义:“马斯洛对那些成功地自我实现的人进行了调查,通过着重研究为这些人的生活带来启发或不断给他们的生活留下烙迹的某些充实时刻(peak-experiences,“高峰体验”),他发现,这些人的动力以及他们对宇宙、事物和人的认知方式具有普通心理学尚未揭示的特征”[4]。
马斯洛的观点尤其在“积极心理学”中得到再现,这种心理学致力于发掘使生活充实、幸福的因素,而不是驻足于探究生活中的病态方面。2004年,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就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5]。他们对包括哲学和宗教性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探究,概述了一些可以使生存更加美好、通过磨练性格而使人更加沉稳的要点。此外,作为这股思潮的另一位倡导者,艾伦·沃特曼(Alan Waterman)重温了亚里士多德的“人的自我发展”(eudaimonia)的重要性,即通过实践诸如默观等人类最为崇高的活动而充实自己的生活[6]。
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特征
彼得森和塞利格曼还依照古典哲学的思考,将亚里士多德和多玛斯所探讨的智德、勇德、爱德、义德、节德和先验性美德放在首位[7]。这些品质是通过人在长期的教育、重要的情感关系、团体生活以及健康和谐的发展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它们能够关护人格的方方面面。
在该研究所展示的主要特征中,幸福与爱密切相关,但这种爱并不是指感官愉悦eros),而是意味着给予(agapē),是一种活出令人满足、持久和稳定的情感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得益于从公共角度来看也具有重要性的相关群体的存在,比如家庭、文化、社会和宗教机构。如果一个孩子在一个情感稳定的婚姻中成长起来,他或她无疑会在学校的认知、注意力、学习和兴趣方面表现出优势,并能以尊重和非暴力的方式与同龄人相处[8]。向那些对个人生活感到满意的群体和个人的提问呈现了以下一些恒定的特征:家庭关系、职业、朋友、健康、表达自己最深切愿望的可能性[9]。
另一项值得关注的研究在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沃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指导下进行。他完成了关于生活质量这一主题的最全面、最广泛的调查,历时75年(1938-2013年),涉及该调查发展过程中的整整几代人。调查样本最初为724人并继而随着其后代的加入而增至2000人[10]。这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总体,涵盖了在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和生活经历等方面具有极大悬殊的情况以及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经济繁荣、消费主义、青年抗议、信息技术和数字革命的个体。这些人中既有哈佛大学的富有者,也有不具备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波士顿穷人。
与此同时,这些人的调研者也已年迈,他们把接力棒传给了其他同事:罗伯特·沃尔丁格是继乔治·瓦朗(George Vaillant)、崔新佳、斯蒂芬·索尔兹(Stephen Soldz)之后第四位接任研究主任的人。该研究每两年准时更新一次;受访者的人生轨迹也同样丰富多彩,他们中既有专业人士、管理人员、著名政治家—包括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也有雇员、酗酒者、吸毒者和精神病患者。他们有些人从最底层登上了国家首脑的巅峰,而有些人则相反,虽起步于顶峰,却随后一落千丈。基于以上原因,这是一个对于人生可能道路的独特调查样本。
决定性参数:关系
研究结论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三个也会在其他研究中重现的教训尤其值得借鉴。
1) 第一个教训与彼得森和塞利格曼所指出的非常相似,即:对生活质量贡献最大的因素是(与各自的亲朋及团体之间的)美好情感及令人欣慰的关系,而孤独则是有害的,甚至成为自我伤害、以至造成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之一。这一情况也出现在英国成立的孤独事务部报告中。数字化新机遇似乎使这一趋势更为普遍[11]。另一方面,冲突型人际关系比孤独更为有害。
2) 第二个教训是,美好而令人满意的情感关系除了让人幸福,还能使人健康长寿。为了检验这一理论之真伪,研究人员假设了参考样本中会在30年后依然健在的50-59岁年龄组成员。此外,那些当时符合幸福标准的50-59岁年龄组成员也是年过八旬之后仍然在世并对自身状况感到满意的个体。“健康”的决定性参数并非体质、体育活动、血液中糖或胆固醇的含量,而是人际关系的质量。在谈到“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时,研究人员所指的并不是不存在争执,而是对人际关系稳定性的信心:“良好的亲密关系似乎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老年病的困扰。某些八旬夫妇尽管会隔三差五地拌嘴,但只要他们感到的确可以在遇到困难时相依为命,这些争执就丝毫不会使他们记恨在心”[12]。
此外,对个人生活的幸福感似乎比服用药物更能带来抚慰。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着他的衰老。最打击人的痛苦并不在于疾病或身体上的衰弱,而是人生目标感的缺失。
亨利·卢云(Henri Nouwen)在参加方舟(L’Arche)团体活动时指出:“在我的团体里,有许多重度残疾者,但他们最大的痛苦并不是残疾本身,而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配或者得不到理解和关爱的感觉。相形之下,接受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或不能自己吃饭要比接受无法对他人产生任何特殊价值容易得多”[13]。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Murakami Haruki)恰到好处地区分了痛苦和苦难迫承受的,但主体的内心评论、其价值世界和动机可以使人对痛苦具有不同的体验。同样的痛苦事件,不同的体验主体会有不同的痛苦感受。正因如此,村上这样观察到:“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但苦难是可以选择的。例如,我们假设一个人这样想:‘我做不下去了,这太费力了’。疲劳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否能够继续承受则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个体”[14]。
3) 历经数十载的该项研究显示了第三个教训,那就是:幸福也能促进智能活力,即对新知识和新体验抱持开放态度的愿望,这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沃尔丁格的团队在完成该项研究后也在思考这些真谛虽然一直为人所知却大多被忽视的缘由。就此,他们观察到了“认知扭曲”、自私自利的自动行为、自我封闭的倾向以及急功近利的心态。当他们向人们提出幸福与什么相关联的问题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当你拿到钱并把它们花在自己身上时。虽然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但却极其根深蒂固。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打破人的偏见比崩解一个原子还难。实际上,人只有在致力于他人的幸福时才会获得幸福。
其他在美国(对这一主题研究最多的国家)进行的研究也同样验证了与此非常相似的衡量标准。按重要性排序,这些标准依次是:1)家庭;2)经济稳定;3)令人满意的工作;4)友谊;5)健康。此外,虽然还有其他显著衡量标准–如自由度和一般参考价值–但它们由于在不同情况中所占比重不同而难以排序[15]。
夫妻之爱至今仍被视为最高价值之一,尤其在与生育和养育子女联系在一起时更是如此,尽管乍看起来这似乎并不符合关于个人自我实现的建议中所固有的快乐和直接满足:“关于幸福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心理幸福感尤其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中会显著下降,这一现象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有孩子究竟是否真的让人感到不幸福。但许多研究表明,不眠之夜和缺少空闲时间并不影响为人父母的充实感,尤其对于那些将子女的幸福置于自身需求之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16]。
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一项对10万人进行的调查中指出,,而是与人际关系的质量有关,其中尤其是婚姻质量[17]。
幸福的阻力
各种研究的结论非常接近于思想史以其他形式所展现的内容:虽然这些方面已经通过某些形式而为人所知,但一种奇特的与之相对的抗衡却总是层出不穷。
研究人员也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结论虽然在每项调查中均得到确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明晰且经久不衰,但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屡遭忽视?关键之处在于这一切所需要的“代价”,诸如所有重大事宜(学习、职业、体育成绩、对承诺的忠诚),它们需要付出努力、专心、舍弃和长久的时间。当一个人无偿地热衷于某件事情时,他就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尤其是体验到“内心的玩味品尝”之美妙,正如依纳爵·罗耀拉所提醒“满足灵魂”(《神操》,第2条)。然而,这一切需要无偿的投入,也不能马上得到的满足;因此,人们会怀疑“游戏是否真的值得这种付出”。在现实生活中,损害生活质量的恰恰是匆忙和占有欲。
自发性并不是处理生活问题的好方法,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教化,并时常展开批判性的探讨。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当今工业化社会的幕后操纵者、大型资本机构以及黑社会组织并不热衷于“幸福”星座所展示的一切,其共同之处是肆无忌惮地追求利润,然后将它们全部花费在自己身上。但结果却总是无法如愿以偿。相反,那些生活幸福的人却并不在意多重报偿。
高质量的人际关系不仅对个人幸福不可或缺,而且也对社团的健康生活至关重要,因为这涉及到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所说的“社会资本”,即:维持社会及其正常运行的关系和利益网络。社会资本“能够使公民更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18]。为此,社会资本可以被视为一个团体的健康指数,因为它提供了能够应对并克服负面事件和悲剧性灾难的抗体。这是生活质量中的一个基本方面,需要首先通过反思来重新获得其核心地位。
一些可能的途径
与大众人群的关系会有助于理解是什么使人在利他的同时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精彩乔治·瓦朗、崔新佳、斯蒂芬·索尔茨和罗伯特·沃尔丁格进行的多代人研究清楚地展示了幸福与培养人际关系的紧密联系:培养人际关系是一种无偿的关护,而不是唯利是图。他们的结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可以是简单地花更多时间与人相处而不是看电视,也可以是通过重新一起做些事情来活跃淡漠的关系,比如一起多散散步、晚间外出,或是与一个多年不来往的家人重新取得联系,因为常见的家庭纠纷会让生闷气的人付出巨大的代价”[19]。与充实生活密不可分的是那种以自己所获得的恩典帮助他人的渴望。
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特别指出了一些在人际关系上做投资的具体途径,它们是:
1) 将税前总收入的5%捐献给慈善机构;
2)抽出一定的时间,为弱者开展志愿性慈善或社会活动,比如前往医院探望病人;
3) 如果有人向你讨钱,试着与他交谈,而不是一味施舍[20]。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正视人生的短暂。面对死亡,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会通过对比而显现,而且往往是下决心采取行动的决定性触发因素。借用马克·吐温之言,即:“生命如此短暂,我们没有时间去争吵、道歉、伤心、斤斤计较。可以说,我们只有时间去爱,一切稍纵即逝”[21]。
欧文·亚隆(Irvin Yalom)通过陪伴一些临终病人而认识到,在这一工作所带来的心理和情感负担之外,还有一种深刻的教诲能够彻底颠覆人们心中的重要价值标准。有一天,一位小组成员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因为他决意将自己对待死亡的方式当作可以传授给孩子们的最宝贵的一课:“我从未遇见比这个人更好的例子来说明幸福感如何通过找到生命的意义而萌生。他也是‘涟漪效应’概念的特出典范,这种效应帮助许多人减轻了对死亡的恐惧。涟漪效应是指我们将自身的一部分传递给其他人,包括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它会像投进池塘里的石子所激起的水纹一样扩散开来,直到消逝不见,但却仍在继续[…]。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分享了他的经历。一位病人感叹道:‘真遗憾,我一直等到现在,当自己的身体被癌症折磨得百孔千疮的时候才学会生活’[…]:虽然肉体的死亡可以摧毁我们,可是,对于死亡的观念却能拯救我们。在我看来,这很好地阐释了一种观念,那就是:既然我们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它,尽可能减少临终时的遗憾”[22]。
思想转化
积极心理学中冉起了指引方向的点点“新星”,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对源于自发性或常识性的评价标准的彻底颠覆。举例来说,许多人会将照顾病人视为令人沮丧或丧失生活热情的事情(每个人本来就已经有那么多需要操心的麻烦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发现自己对他人的重要性的感觉是生活乐趣和满足感的源泉,而这似乎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赋予我们的:“长期的社会工作有益于我们自身。可以得到证实的是,与单独从事令人愉快的活动相比,为公共利益而行动不仅降低抑郁和不适的发生频率,而且还会使人们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此外,更重要的是,与最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形影相随的空虚感也会随之而减少”[23]。
“施予比领受更为有福”(宗 20:35)。此教诲往往被忽视,但它却抓住了幸福的真谛:当一个人努力为他人的幸福着想时,如花似锦的幸福就会不期而至。一切最重要的东西都会不期而遇,你会在达到忘我的境界时认识到它们。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指出,通往幸福的大门是向外开的:那些把门朝着自己拉的人反而会不可逆转地将它紧紧关闭[24]。这个画面是对“认知扭曲”和对生活的错误期望的一个生动写照。,这个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当你不再蜷缩于自我及个人问题中,而是不求回报地去关注他人的时候。
- 参见G. Cucci, La forza dalla debolezza. Aspetti psicologici della vita spirituale, Roma, AdP, 20224, 179-186; 201-210. ↑
- D. T. Campbell,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evolution and between psychology and mo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1975) 1104. ↑
- I. D. Yalom, Momma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ales of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22 (意文版:Il senso della vita, Vicenza, Neri Pozza, 2022). ↑
- A. Godin, Psicologia delle esperienze religiose. Il desiderio e la realtà, Brescia, Queriniana, 1993, 84. 参见A. H. Maslow,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2, 67-96 (意文版:Verso una psicologia dell’essere, Roma, Astrolabio-Ubaldini, 1971). ↑
- Ch. Peterson – M. E. P. Seligma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4. ↑
- 参见A. T. Waterman, «The relevance of Aristotle’s Conception of Eudaimonia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Happiness», in Theoretical &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7 (1990/1) 39-44; Id. (ed.), The best within us: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eudaimonia,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
- 参见N. Park – Ch. Peterson – M. E. P. Seligman, «Strengths of character and well–being», i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3 (2004/5) 603-619. ↑
- 参见I. Boniwell, La scienza della felicità. Introduzione alla psicologia positiva, Bologna, il Mulino, 2016, 123; M. Seligman, Authentic Happiness: Using the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to Realize Your Potential for Lasting Fulfill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02, 188. ↑
- 参见R. Layard, Felicità. La nuova scienza del benessere comune, Milano, Rizzoli, 2005, 84. ↑
- 参见http://adultdevelopment.wix.com/harvardstudy/; R. J. Waldinger – M. S. Schulz,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Social functioning, perceived health, and daily happiness in married octogenarians», in Psychol Aging, 2010年6月25日, 422–431. ↑
- 参见»Effect on loneliness on local communities«, in https://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CDP-2017-0221/CDP-2017-0221.pdf/; S. Turkle, Insieme ma soli. Perché ci aspettiamo sempre più dalla tecnologia e sempre meno dagli altri, Torino, Einaudi, 2019; M. Spitzer, Connessi e isolati. Un’epidemia silenziosa, Milano, Corbaccio, 2018. ↑
- R. J. Waldinger – M. S. Schulz,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cit., 427. ↑
- H. Nouwen, Sentirsi amati. La vita spirituale in un mondo secolare, Brescia, Queriniana, 1993, 72 s. ↑
- H. Murakami, L’arte di correre, Torino, Einaudi, 2009, 4. ↑
- 参见http://cep.lse.ac.uk/layard/annex.pdf ↑
- J. Retzbach, «Il senso della vita», in Mind, n. 164, 2018, 31. ↑
- 参见J. L. Freedman, Happy people: What happiness is, who has it, and wh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
- R. D. Putnam, Capitale sociale e individualismo. Crisi e rinascita della cultura civica in America, Bologna, il Mulino, 2004, 345. 参见G. Cucci, «Il capitale sociale. Una risorsa indispensabile per la qualità della vita», in Civ. Catt. 2019 I 417-430. ↑
- R. Waldinger, «What makes a good life? Lessons from the longest study on happiness», in https://www.ted.com/talks/robert_waldinger_what_makes_a_good_life_lessons_from_the_longest_study_on_happiness ↑
- 参见M. Seligman, Imparare l’ottimismo. Come cambiare la vita cambiando il pensiero, Firenze, Giunti, 2013, 374 s. ↑
- M. Twain, Lettera a Clara Spaulding, 1886年8月20日。 ↑
- I. D. Yalom, Diventare se stessi, Vicenza, Neri Pozza, 2018, 213 s。文中斜体。 ↑
- M. Seligman, Imparare l’ottimismo, cit., 375 s. ↑
- 参见S. Kierkegaard, Aut-Aut, in Id., Opere, Firenze, Sansoni, 1972,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