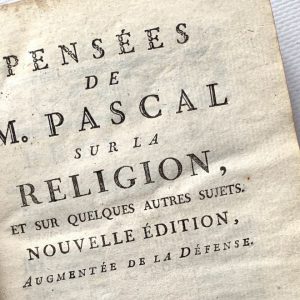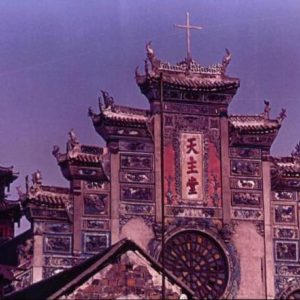圣多玛斯是法学家玛?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昔日法学院创立之初[1],曾重新使用(第六世纪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命令汇编的)“法学家学说汇纂”(Digesto)作为研读罗马法的基本读本。后世根据这个读本建立起现代民法和教会法的庞大法律结构,那是个新的社会原理原则秩序,注定日后将广为发展。多玛斯·阿奎那在生那个世纪是法学研究、阐述法学概念并纷纷成立法学院的蓬勃世代。当初一切尚未定型而且混乱不堪,至今仍然影响着大众的生活。多玛斯在他巨作中的诸多论点充分显示他对此的深切了解认识[2]。
当然,多玛斯不是今天我们认为的狭义的法学家:其实,他具有基本上完整统合的知识,而我们今天却把这种统合知识所含括的各部分孤立起来,其支离破碎之至于今为甚。从另一方面看,不同学科之间的区别或划分乃来自这些学科从基础知识所取得的独立自主性,对于多玛斯和他那时代来说,这种基础知识就是神学。于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解码就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概含人类各门知识却互不沟通的百科全书(l’enciclopedia)。然而,中世纪特有的文学产物“纲要(Summae)”与其后的百科全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解说现实的唯一原理原则“天主”,祂使人类全部知识融合贯通成一体并赋予意义。事实上,多玛斯肯定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都从与天主的关系为出发点来谈论:或因为是天主本身,或因为天主乃一切的根源和归属”[3],这正指出多玛斯阐述的学科秩序(ordo disciplinae)。足见多玛斯是神学家,而非法学家,虽然如此,“法”(diritto)并没有被排除在他的学术思考中。
思考差别
为一个生活在十三世纪的人来说,谈论经济、人类学或政治问题而不涉及天主,实在不可思议,对“法”(diritto)来说也是如此。然而,这并不意味多玛斯不谈这些议题,而是他以“不同的方式”来谈,至少我们的观念认为如此。即便在探讨法的哲学(la filosofia del diritto)方面,一如探讨“法”本身及其历史那样,似乎也需要那界定得好的“洗净内在(lavacro interiore)”[4],以便怀着宽大的心境来思考其“差异”(differenza)[5],藉以避免将那些我们自以为当然的视为正确的或可以接受的,从而保持开放的态度重新思考、重新讨论和相对化我们的文化或认识论模式
多玛斯讨论法律(legge 或 lex)问题见于《神学大全》第二集的第一部,它检讨人的超性德行(枢德virtù cardinali)和自然(本性)德行(morali naturali)。这些德行是理性受造物“人”跟随自己天性的目标回到造生他的天主那里的步骤[6]。至于“法”(diritto 或jus)则在第二集第二部讨论,它检视恩宠在人心中的活动以及天主赐给人并引向祂的三超德(virtù teologali),即信、望、爱三德的恩典。相对今日而言,把法律问题规划在神学人类学中乃是第一个重大的差别。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第二个重大的差别乃是多玛斯认为的司法经验乃在法律(legge)和法(diritto)两个层面之内进行的,但两者绝互不叠合,它们一如椭圆形的两个焦点[7]。可是在我们的思维世界中法律大致与法叠合,就连法学院学生中也没有几个能够完全指出其不同。其实,在这普遍混乱之下隐藏着某种更深入的问题,即:是否西方法(diritto occidentale)的历史是一条从法走向法规的路程[8]。椭圆形已经失落它的两个焦点而成为一个同心圆(cerchio):“等同法律的合法性似乎只流为司法计量的单位,它危害了符合法的正当性”[9]。可是二战后的一些宪法重新将古时的法(jus)与法律(lex)相提并论,甚至居于法律之上,于是同心圆又变成椭圆。事实上,“国家制定法律,但不制定法,因此,国家和法律处于法之下”[10]。在盎格鲁萨克森司法界中,这被称为“法律规则(Rule of Law)”。
法律经验的核心:法(jus )
我们最容易铸错的就是把法这个名词视同我们的主观权利(diritto soggetivo),这乃是典型的现代概念。在中古哲学、特别是在威廉·奥坎(Guglielmo Occam1332年)的所著《九十天之作(Opus nonaginta dierum)》巨作之后,这个意味着“合法的权(potestas licita)”[11]的名词在十五至十七世纪西班牙文化运动中得到完全的肯定,这在弗朗西斯科·苏阿雷斯(Francisco Suárez)的思想中更为明显,他把合法的权定义为伦理能力(facultas moralis)[12]。从此,这个观念经由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Codificazione napoleonica)变成为现代的词汇。于是,这个词汇所指的不外乎“行使由司法条例保障的主体意志,以满足个人利益的权力”[13],它是某种完全“主观”的东西,它由司法条例授予并予以保护,其唯一的来源根据就是立法者的意愿。
然而在中世纪的司法界,所谓的法(jus)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尚未存在国家这个政治体制,因为这种中央集权而且独占的权力结构乃是现代世界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所谓的国家乃是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la pace di Vestfalia)、政治完全进入现代化之后才出现的。当时所谓的政权还过于脆弱,没有能力自立威望,而司法界的基本核心则是一种客观上分摊世界财物的“东西”,它不是某位立法者的意愿,也不是由法律认可保障的主体本身的意愿。然而在中世纪,“法是个事实存在的东西,它不是政权所创造的,政权也不企图创造它,更没有能力创造它;政权仅能说明和证实它而已”[14]。
法(jus, diritto)是“正义(义德)的对象”[15],是应归于他人的事物,因为正义之德在于给他人应有的,这是正义的做法[16]。这里我们重新发现乌尔皮亚诺(Ulpiano)的定义,即罗马帝国和中古世纪司法体系的表达方式,也是相反现代欧陆系统的理论和法学体系的表达方式,它所依据的乃是一个详尽不漏、代表全能立法者意志的最高唯一法典(Codice)。这就是有待重视的第四个重大差别。
此外,法(jus)明显被定义为公正合理事物的本身(ipsa res iusta)[17]。客观地说,法在人的理性作为之前即已成立,它是一种来自事物自然的必要关系:在任何分析之先,且异于分析,已经存在着事物的合理秩序,别的都不是。它表达了亚里斯多德的公平交易和分配正义的准则。
这在今天仍然如此吗?
于是,根据公平交易(公平交换,giustizia commutativa)准则,在今天也一样,客观合理的事物秩序就是那保障受到不合理损伤的人获得相称的补偿。就这样,从数量名义来看, 伤害者之间进与出的商数关系符合数字单位与公平。显然地,我们在谈契约外的责任,这在意大利由《民法》第2043条来规范:“任何给他人造成不正当损害的蓄意或非故意事件,要求肇事者赔偿损失”。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立法者如是说,但也因为是真实的,所以立法者如是说。如果有谁因为过失,即疏忽,或预谋,或恶意,而给我带来损害,他必须补偿我: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我的财产该遭到不正当的损害,而补偿必须涵盖我的财产遭受的全部损失。这就是多玛斯所谓的公平合理事物的例子,合理分配世界的财物。
公平交易原则在买卖中最为明显:物品价格的合理在于价格符合该物品本身及所付出的劳动的价值,以及售者的合理酬劳。不成比例的价格是不正当的,任何买者都了解此事:但也会发生买卖虚荣这类不真实的事,就像一个产品的品牌(griffe)变得比实质更重要这类事。在这种情况下,合理价格的理论在真实的经济中可能带来巨大的冲击,它不任由市场供求的原则来玩弄。于是,面对出租公寓的实际状况,租赁契约不能因为求租者众而产生付出更高租金的竞争,而提高远超过公寓价值的租金。为多玛斯来说,这就是“法”如何与“伦理道德问题”、也就是与“正义(或义德)”相系的实例,它不能仅以合法性来强制。
同样,我们认为高于合法利率的高利贷乃不合乎正义。事实上,合法的利率已经抵偿贷款存置及其贬值的损失。然而,放高利贷者因要求不正当的利息而赚取无理的工作所得,这在多玛斯的思想里不是合乎正义的事,因为所取的不符合所给的[18]。的确,正义合乎传统天枰(秤)的形象:给与取之间相等,支轴两边的盘子即平衡。
法律预定的因错误、暴力或蓄意之故而废除契约的措施,乃是立法者的选择,他给公平交易原则具体的形式。在此我们似乎又听到多玛斯的话:“法或正义之事是以某种适当的方式谋取与他人平衡的行动。可是一件事物能以两种方式与某人取得平衡:第一种是根据这事物的自然本性,例如一个人付出多少,就收回多少,这就是所谓‘自然的正义’;另一种方式是由于约定或由于大家的同意而使一件事物与他人取得平衡或相等,例如:一个人如果能得到这么多,他就会满意。而这样的事也用两种方式来完成:第一个是用私人的约定,例如在私人之间,经由合约而加以订定;第二个是经由公众的约定,例如全体民众都一致认为经由某适当的事物,或是经由负责管理人民者做了这样的决定,就算是与别人平衡或平等。这就是所谓的实证法”[19]。于是我们发现一件很美好的事:“正义的普遍形式就是平等,在这个形式中公平交易和公平分配两相谋和”[20]。平等(平衡)和正义(义德)是同一个关系的两面:正义扮演平等的面貌,而哪里有平等,这平等就变容为正义。事实上,正义的任务就是“实践平等,并使之不受损”[21]。
到此已清楚,多玛斯的自然法(giunaturalismo)理念不但不使民法或成文法沦为多余,反而使其成为必要。
从法(diritto)到法律(leggi)
由此可见,在多玛斯的思想中首先存在着一种公道(giusto),一种本质上(per natura)应当之事(dovuto);其次才有我们今天要说明的根据私人之间的同意所签署的“契约”[22]而来的公道;最后就是立法者依据成文法而决定的应当之事。然而,法与法律并非同一回事:“正确地说,法律并非法本身,而是法的某种理由或边缘的规则”[23]。法律属于理性,是抽象、科学、实用、三段论法演绎出来的规则,它可以建立其他相等的“合理事物”;然而公道为才智者及其行动所接纳,是对整体事实及其目标的理解[24]。
现在我们到了谈法律(leggi)的时刻,此处我们发现另一个重要的差别。“在现代的法哲学(filosofia del diritto)中,司法规律(legge giuridica)就是最高的法律(Legge per eccellenza);在这最高法律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消失,至少黯然失色…。然而为多玛斯来说,法律的概念极其广泛…,司法规律仅是许多法律形式的一种而已。换句话说,当我们的法哲学家撰写法律时,他们想的仅是非常狭隘的事实,即整部法典中的一条法规而已;然而多玛斯描写法律时,他想的则是宇宙关系中一个巨大的系统”[25]。
事实上,在多玛斯的思想中,“我们所有的法律都彼此循环畅通,其起点和终点都是天主。法也经由永恒法、自然法和成文法这三位一体(三部曲)回到它的最原始根源天主那里。祂是最高的立法者天主;铭刻在人心中、参与神的法律的自然法;一个符合与自然法细节的成文法:这就是多玛斯伦理-司法体系绝好的和谐。所以,这是人类学与天主乃人类普遍法律之源(teonomica)一致的观点,因为正义(giusto)问题不能完全脱离与神学问题的关系而自行解决”[26]。
现在我们快速反观一下多玛斯思想体系中的法律种类。
一个美好的秩序
多玛斯提供给所有法律一个共同的定义:“法律是理性的秩序,由照顾团体者颁布,以公益为目的”[27]。因此,法律是秩序,而非发号司令。法律显示了先于它(法律)的事物和正义的秩序,并明确说明这秩序,而且几乎延伸它:事实上,法律必须根据事物的需要和目的,即它们的本质,来制定合乎我们所谈及的正义和该当之事的自由行动规则。再说,多玛斯借用他直译的亚里斯多德的概念说:“人的理性不是事物的尺度,甚至与此相反”[28]。附带地我们也看到“秩序”(ordine)这个名词也遭到偏解,误以为发号司令(comando),它不再以事物为本,而以立法者的意志为依据:由此而产生不受任何约制的专制国家和专制政权,只仗恃自己的效力而不听从他方,于是法(diritto)的任何地位立场都成了强制接受(imposizione)[29]。
多玛斯看到的是整个世界,大宇宙如小宇宙,由理性的秩序所带动,但这里所说的理性乃是天主的理性,而存在于天主内的这个统理万事万物的秩序或计划乃是世界最高的统治者,真正具有法律的本质,被称为“永恒的法律(legge eterna)”[30]。这个永恒的法律奠定其他参与其中的自然法和成文(实证)法,一如钟表内最外在的齿轮带动其他的齿轮运转,使之成为外齿轮运转的一部分。再举另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自行车在转换变速轮时,第一个齿轮带动其他的齿轮而决定其速度。
永恒的法律为我们来说还有另一个基本的差别,不仅在神学的重大意义上如此,在认识论上也一样。事实上,我们并不认识永恒的法律,只有天主和真福者才认识[31]:因此,永恒的法律为我们乃是一个奥迹。这个名词不仅指所有我们不认识的,它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就因为我们不认识它,所以永恒的法律让我们所有的认知成为问题,它阻止我们把从永恒法律而来的自然法和人为的成文法僵化为固定的概念,并让我们继续重新定义它们,不断地予以反思。与之相反的则是事实的抽象理性,天真幼稚的详尽理性,是科学或理性的意识型态,人经常为了这个意识型态而牺牲了事实。
当存有,也就是奥迹的最后框架,消失后,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肯定地说:“在我看来,戈罗吉奥(Grozio)正确地使经院学派的天主永恒法则与社会性原则相吻合”[32]。于是,在谨慎认知、每次可以查证而且总可以指出问题之后,我们得到永远无往不利和一劳永逸的必要结论,一如数学定理一样。据此,从良好的社会关系原则产生拿破仑民法的三大支柱:财产权的绝对性,具法律力量的契约,损害的赔偿。
历史中,自然法(giusnaturalismo)的漫长旅途在理性法(giusrazionalismo)中粉碎而告终[33];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法将威信扫地,因为不难发现人的义务和权利不是始终在任何地方都平等,这点圣多玛斯也知道。
自然法(La legge naturale)
于是,从永恒法而产生自然法,正如所定义的永恒法显示在理性的受造物身上(participatio legis aeternae in rationali creatura)[34]。所有的受造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永恒法或天主对世界的治理,而理性受造物(人)比其他各种受造物更为如此。事实上,如果人属于非理性的受造物[35],他就无法表达法律,因为法律属于理性范畴;然而,有理性的受造物经由他的智力和理性参与这个范畴,这样的参与就称作“法律”[36]。为此,人参与天主的圣意,将之展现于世界中,“因为他藉着提供给自己和他人的所需来参与天主的圣意”[37]。人因参与天主的圣意而产生救济行为:有所谓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或 Stato assistenziale)的世俗照应(provvidenza laica),这并非偶然。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多玛斯思想中许多现代化的种子之一。
据此,人与所有受造物一样,他的本性倾向于保存自己的存在;于是产生了不但禁止损害生命,而且必须增进有益于生命发展的戒律。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共同点,也产生了男人与女人结合,照顾幼小,给以教育和其他类似的义务。又由于人是理性的存在物,所以他倾向于度社会生活并渴望认识天主的真理[38]。因此,在多玛斯的思想中我们看不到现代特有的自然与文化、自然与历史、或自然时间(也称为自然的状况,它常被与自然本身混为一谈)与国家时间等等之间的冲突对立。这些对立导致自然主义(naturalismo)和历史循环论(storicismo)之间的自相矛盾。事实上,就如我们在前篇文章中谈过的[39],“自然并非某种业已给予或已经完全展露的东西,而是仍有待实现之物”[40],因为这是每个受造物的终向。为此,自然法的第一个规诫就是:“法律的首要诫命乃行善避恶,并追求善;自然法其他所有的规律都建立在此基础上”[41]。
所以,自然法无非是有理性的人以其本性动力、基本倾向和首要需求而表示出来的神的秩序。据此,自然法和表达这个法并指出其要求的成文法都以天主本身为其本体基础(fondamento ontologico)。为此,法律若从它的根源看,可以称为“先验的”(trascendente);从它的近源、即事物的秩序看,则是“客观的”(obiettiva);由于它(法律)是由人本性及其社会生活固有的原则组成的,所以是内在的(immanente);又由于它是理性的产物,所以是理性的(razionale)[42]。这里又有另一个基本的差别: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法律只是属于人,而非天主,而因为天主已被移去,更不属于自然,即使我们认识科学自然法(le leggi naturali scientifiche),但它不是自然法,因为科学自然法说的是另一回事,与自然法不相关。
人的成文法(La legge umana positiva)
为多玛斯来说,成文法既是神性的,也是人性的。但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详述多玛斯有关成文法的全部理论和与之相关的问题,例如:公益的政治司法由谁来主持,统治者与受统治者的关系,法律的颁布,法律是否使人变得良善及约束人的良知,法律应以一般和抽象的方式还是以法官制定的法律(judge-made Law)来理解等等。我们也不讨论欺骗法律行为(negozio in frode)和以习惯作为法律的根据或特免之类的问题[43]。本文仅谈些许一般性的问题。
在《神学大全》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专门谈人的成文法本身及其权力和变化的问题。但谈论永恒的法律和自然法的问题分别只有一个。“法”(diritto)或“成文法”(legge posotiva)两个名词之所以广获认同大都得力于多玛斯,他从拉丁文翻译的亚里斯多德著作汲取精华:“多玛斯理论最杰出的贡献就是他以比其他任何司法理论更可靠和更有权威的方式,明显地指出自然的必要和法律权威乃法的根源”[44]。
多玛斯有关成文法的思想理论主要来自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尤其是《尼科马克伦理学》(l’Etica Nicomachea)和《政治》(Politica)两书,他从人的本性演绎出城市的体制。然而,社会形式和其具体组织的根源不是自然,而是理性活动;因此,社会形式和其具体组织是自然与理性、必然与自由共同作用的结果。奥斯定和早期中世纪的概念从此被超越,根据他们的观念,法律乃是一种必要的坏事,是天主上智为了处置人的邪恶而制定的[45]。于是,我们从一个天主上智安排的神圣权力概念进入一个更为清醒、却不因此而漠视或对之不恭的概念。
为此,立法工作是向自然法敞开研究,寻求避恶行善方法的延伸。这项工作从来不会正确无误的:事实上,这项研究是在实用理性的范围内进行的,它与理论性研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涉及人的行动方面,而人是自由且易变的。“实用理性的对象仅限于有待行使的行动,这些行动都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而非思辨理性的对象,即必要之物。所以,人的法律不能没有错误,它们在理论科学中得到结论。然而,也要求所有的准则基本上都是无误且确定的,但只按照它的类型所表现的即可”[46]。
从自然法产生成文法的过程一如三段论法的结果一样,例如说“不能杀人”的诫命乃来自不能行恶的普遍性诫命;或如在艺术方面那样,从范例到特定的个别作品;又如建筑工程应用一般性的结构于具体的房屋。于是,自然法确立谁违法该受惩罚,但这样的法律运作需由人订定的法律来说明该如何执行[47]。同样地,就如前面提过的,为了自然的公道,契约意愿的形式签署要求签约者具体的临在才得以进行,而且不受到错误、暴力或欺骗所污损;之后,如果因为进一步的考虑而发生契约无效或可废除的情况,则由成文法的立法者来确立签约者该遵守的规定。
结论
的确,圣多玛斯有超凡的法学智慧,我们当代的法学者当然可以从他的智慧汲取灵感。多玛斯并不是法学家,也就是说,他既非法律专业人士,亦非法学方面的专家,但他在谈论法的时候显出极大的才华,这是他那时代成熟的果实。多玛斯是一位神学家,他把对天主圣爱及天主临在的热情探研连接到人类各方面的知识。如果我们愿意把圣依纳爵罗耀拉的话用在他身上,我们可以说圣多玛斯的确在任何事物上寻找天主并找到祂。他是基督信徒知识分子杰出的榜样。
- 在意大利,法学院最早于1088年成立于博洛尼亚(Bologna),之后于1222年在帕多瓦(Padova)成立,随之于1224年在拿波里(Napoli)设立。 ↑
- 多玛斯从他的《论语录(Commento alle Sentenze)》直到《法律纲要(Summae)》,都在显示他完全掌握司法问题,例如司法权或教会管理权与神品圣事及忏悔圣事之间的关系议题。关于这点可参见O. De Bertolis, Origine ed esercizio della potestà ecclesiastica di governo in san Tommaso, Roma, Pontificia Università Gregoriana, 2005. ↑
- 见多玛斯·阿奎那《神学大全》, I, q. 1, a. 7.。 ↑
- P. Grossi, L’ordine giuridico medievale, Roma – Bari, Laterza, 1996, 10. ↑
- A. M. Hespanha, Introduzione alla storia del diritto europeo, Bologna, il Mulino, 2003, 26. ↑
- 参见《神学大全导论(Introduzione a Summa Theologiae, I, q. 2)》:“圣道的主要目的在于引人认识天主,不仅天主本身,而且认识祂是万物、尤其是有理性的人的原始和终结…。我们首先谈天主;其次谈理性的受造物走向天主的活动;最后谈基督,祂既然也是人,所以也是我们走向天主的道路”。这都得力于马利-多米尼克·塞努神父(p. Marie-Dominique Chenu)以一切都从天主出发并归回天主(l’exitus a Deo e il reditus in Deum)作为解读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的关键。但这并非唯一可能的解读。参见M.-D. Chenu,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saint Thomas d’Aquin, Paris, Vrin, 1954, 263。 ↑
- 参见O. De Bertolis, L’ellisse giuridica. Un percorso nella filosofia del diritto tra classico e moderno, Padova, Cedam, 2011. ↑
- 参见V. Varano – V. Barsotti, La tradizione giuridica occidentale, Torino, Giappichelli, 2006, 124. ↑
- 见G. Zagrebelsky, La legge e la sua giustizia, Bologna, il Mulino, 2008, 88。此书第二章很有意思的标题为“从法到法律”(Dal diritto alla legge),它指出根据十九世纪的制定,将法置于法律的顶点。此外,本书作者又在该书第126页观察到“立宪主义的赌注全在于:作为法律的宪法能变成为法”。 ↑
- 这段话取自考夫曼(Kaufmann)所言“Die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 ”(1927),录于Grossi神父所著Prima lezione di diritto一书中, Roma – Bari, Laterza, 2003。 ↑
- 这个名词在 F. Todescan,所著Etiamsi daremus. Studi sinfonici sul diritto naturale(Padova, Cedam, 2003, 97,)一书中引用过;该书又援引M. Villey所著La formazione del pensiero giuridico moderno(Milano, Jaca Book, 1985)的思想,特别见于196-224, 458-466 e 555-580诸页。然而,为《L’idea dei diritti naturali. Diritti naturali, legge naturale e diritto canonico 1150-1625 , Bologna, il Mulino, 2002》的作者B. Tierney来说,应该是早在Occam之前约150年的Uguccione d’Arezzo 就使用过同义的名词。参见 M. Barberis, Europa del diritto. Sull’identità giuridica europea, Bologna, il Mulino, 2008, 138-141。 ↑
- 参见F. Suárez, Trattato delle leggi e di Dio legislatore, I, Padova, Cedam, 2008, 32. ↑
- A. Trabucchi, Istituzioni di diritto civile, ivi, 1980, 45. ↑
- P. Grossi, L’ordine giuridico medievale, cit., 135. ↑
- Sum. Theol., II-II, q. 57, a. 1. ↑
- 参见《神学大全》II-II, q. 58, a. 11: «正义的特定行为无非是还给他人应有的(L’atto specifico della giustizia non consiste in altro se non a rendere a ciascuno il suo)». ↑
- Sum. Theol., II-II, q. 57, a. 1, ad 1. ↑
- 此处之所以谈高利贷,因为它与天主的诫命有关:“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创3:19)。 ↑
- Sum. Theol., II-II, q. 57, a. 2. 一个自然正义的人,一个心存平衡平等的正直者,他主持借贷关系、伤害赔偿、无端致富和利息的纪律,使之清楚易懂。参见M. VILLEY, La formazione…, cit., 39。 ↑
- Sum. Theol., II-II, q. 61, a. 2. 公平交易(或称交换正义)是在私人交换中进行的,而分配正义则主导公职(酬劳)的分配。为此,在民主体制中,公民之间自由的有效平等是基于国家体制建构,所有公共行动都是以此为准则。 ↑
- 《神学大全》II-II, q. 79, a. 1, ad 1: «facere aequalitatem […] et factam non corrumpere». ↑
- 此处,我们可以提及契约在古时的定义为私法(lex privata)。 ↑
- 《神学大全》., II-II, q. 57, a. 1, ad 2: «Lex non est ipsum ius, proprie loquendo, sed aliqualis ratio iuris». ↑
- 因此,为多玛斯来说,自然法与自然法规不相同。我们可以肯定,在多玛斯的思想中存在着一致和均衡,所以法律之于法就如理性之于理智,就如存在之于实有的行动。事实上,如果没有相似的名词,我们就不会有相似的概念。关于这点参见O. De Bertolis, Il diritto in San Tommaso d’Aquino. Un’indagine filosofica, Torino, Giappichelli, 2000, 85-94. ↑
- G. Graneris, Contributi tomistici alla filosofia del diritto, Torino, SEI, 1949, 13 s. ↑
- R. M. Pizzorni, «Diritto naturale e revisione del diritto canonico», in Apollinaris 51 (1978) 31.。我愿一提,当我还是帕多瓦大学法学院学生时,这段文字让我爱上了多玛斯的思想,至今不渝。 ↑
- 《神学大全》 I-II, q. 90, a. 4: «Lex est rationis ordinatio ad bonum commune, ab eo qui curam commmunitatis habet, promulgata». ↑
- 《神学大全》I-II, q. 91, a. 3: «Non ratio est mensura rerum, sed potius e converso». 这个观念让我们避免任何意识形态,即让我们不把我们狂妄的想法或理由当作衡量事物的标准,但以现实作为基本认识的准则。 ↑
- 参见N. Irti, Nichilismo giuridico, Roma – Bari, Laterza, 2004, 35.从这个角度看,国会本身的运作成为毫无内容的形式主义,它仅在证明对某个法规的假设获得多少同意而已(参见注47)。据此,“法规的价值效能与意志相符”(参见137页)。“至此法律已无存在的意义。法律缺乏存在的理由,它将自身完全交付于强制者的力量:没有任何更高的原则足以更正它(同88页)”。其实,为实证主义者来说,宪法应该被视为高于法律的原则。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不能否认强制或发号司令的价值,但为多玛斯来说,有效的原则该是“因为合理正确所以才是法,而非因为强制而成为法” (ius quia iustum, e non quia iussum)。 ↑
- 《神学大全》I-II, q. 91, a. 1. 永恒的法律与天主圣意是同一件事。 ↑
- 参见《神学大全》I-II, q. 93, a. 2: «同样地关于永恒的法律:没有人可以认识其本身,除了那能看到天主本质的真福者»。 ↑
- 托德斯坎(F. Todescan)在他的《司法经验批判之旅( Itinerari critici dell’esperienza giuridica), Torino, Giappichelli, 1991, 52》中引述莱布尼兹(G. W. Leibnit)全集( Opera omnia)的话说: «我以为戈罗吉奥(Grozio)当然把经院哲学家心中的天主永恒的法律与社会公共道德原则视为一致(Recte Grotius meo iudicio scholasticorum Dei legem aeternam cum principio socialitatis coniunxit)». 于是,这位荷兰德夫特(Delft)的思想家(Grozio)成了中古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他在《论战争与和平的法律》n.11中表示:“即使天主没被给予(或说如果我们不认识天主)«etiamsi daremus Deum non esse»”他仍欲寻求一个有效的司法秩序。这标志了一种撇开信仰不谈的思想的开始。然而马里旦(J. Maritain)在他的《自然法九课, Nove lezioni sulla legge naturale, Milano, Jaca Book, 62) 》中指出:“理性主义以戈罗吉奥短短的一句话渗入自然法的概念中…,这是永恒理性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地震。天主只不过是这个秩序的保证者”。然而,“自然法因着永恒法律而承担义务,它从神的法律汲取理性的特征,也因此从神的法律汲取其法律本身的真正本质”。 ↑
- Jean Barbeyrac在S. Pufendorf所著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Francofurtum, Ex officina Knochiana, 1712, XIX的法文版序言中写道:“我胆敢说,如果这些有待逐一进行的科学诸原则彼此结合在一起,正如必要的,而且予以全力扩大伸延,必将因着它们彼此相关的可见后果而得出每个人的义务,不论他身居何处”。» 参见 A. Arbus, «Humanisme et sagesse juridique», in Revue Thomiste 58 (1950) 608, nota 1。 ↑
- 《神学大全》I-II, q. 91, a. 2: partecipazione della legge eterna nella creatura razionale. ↑
- 参见《神学大全》I-II,q. 91,a. 2, ad 3. ↑
- 参见《神学大全》I-II, q. 90, a. 2, ad 3. ↑
- 《神学大全》I-II, q. 91, a. 2: «Ipsa fit providentiae particeps, sibi ipsi et aliis providens». ↑
- 参见《神学大全》I-II, q. 94, a. 2。 ↑
- 参见O. De Bertolis, «Esiste il diritto naturale?», in Civ. Catt. 2024 III 119-129. ↑
- E. Berti, «Il concetto di ordine naturale», in Studium 84 (1988) 509. ↑
- 《神学大全》I-II, q. 94, a. 2. ↑
- 参见 R. M. Pizzorni, «La lex aeterna come fondamento ultimo del diritto in San Tommaso», in Aquinas 4 (1961) 82. ↑
- 这些都是极有意义且现实的问题,在《神学大全》第一集第二部分第90至97议题中谈及。 ↑
- M. Villey, La formazione…, cit., 154. ↑
- 参见Isidoro di Siviglia, s., Ethimologiae, 5, 20: «法律之订立乃是为了以它的慑服力来抑制放肆,俾善良无辜者即使生活在犯罪者中也能平安无事,也令那些罪犯因着审判的恐吓而不再行恶»。圣奥斯定说:“所谓的王国,要不是大规模的暴力是什么?” (Agostino d’Ippona, s., De civitate Dei, 4,4)。 ↑
- 《神学大全》I-II, q. 91, a. 3, ad 3. 理论科学一如数学,是那些从原理开始而无误地推论到必要的结果。参见《神学大全》I-II, q. 90, a. 2, ad 3: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根据理论理性而肯定确立,除非经由最原始的、人力无法证明的原理来解决;同样地,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根据实用理性来肯定确立,除非指向最后目的,即公益»。于是,在《评尼科马克伦理学 (Comm. Eth. Nic., 7, lect. 8)》书中这么说: «行动的动源来自行动欲达到的目标:它与‘假设’有相同作用,亦即数学所显示的原理»。参见《神学大全》I, q. 5, a. 2, ad 1: «目的就是众原因的原因(Finis est causa causarum ;Il fine è la causa delle cause)»。 ↑
- 参见《神学大全》I-II, q. 95, a.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