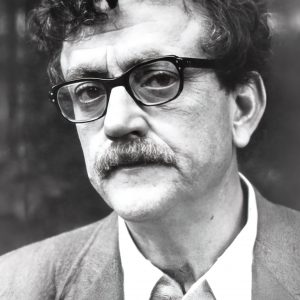教宗方济各2015年5月24日公布他的《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通谕时,给天主教社会训导推了一把力,同时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因为这道通谕不仅以全球天主教徒为对象,也向全人类说话。
《愿祢受赞颂》通谕获得全球媒体广泛的报道和学术界热烈的讨论,这为一道教宗的文献来说绝非寻常。通常,少有教会的文件吸引非教会新闻界人士的注意,就连那些“有立场的新闻报纸”(giornali di riferimento)也只不过报道文献公布的消息而已。然而,《愿祢受赞颂》通谕却有所不同,它所谈论的问题激起了广泛的关切,以致梵蒂冈新闻室不得不召开记者会以扩大消息的覆盖面。正因为这道通谕在巴黎全球气候峰会召开前几个月适时公布,所以也促使它广受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激起公开热烈讨论以及教宗方济各本身深孚众望似乎让这道通谕成了世界关切的焦点。
今年,美国许多耶稣会创办的中等和大专院校都举办了工作研习会,讨论了这道通谕带来的影响[1]。这道文献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受接纳上都吸引了传播学界的重视,这绝非偶然。本着这种重视的精神,本文设法探讨相关的研究,例如:通谕作为环境传播的范例;新闻报纸对该文献报道的程度;媒体对它所进行的种种分析(特别是文辞上的分析);医学、教育、对话和社会传播等方面对通谕的反应;最后就是通谕的影响及其在传播实务如策略传播和销售学(marketing)上的应用[2]。
环境传播
有一个研究传播的领域特别专注环境,它调查传播对公众的影响,对政策的形塑以及推动可行的办法(sostenibilità)。在这个领域内各式各样的传播实务各具角色:新闻学,以推广为目的的大众及社交传播媒体;促使关切(sensibilizzazione, advocacy)以推动适当的解决之道;提出问题及行动策略的政治与科学传播。
学者们很快地在《愿祢受赞颂》中发现一个环境传播的范例,因为教宗方济各在这道通谕中提醒人们关注生态和与之相关的伦理迫切问题。比方说,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把这道通谕定义为“教会信仰对气候变化问题空前的重要答复”[3],他发现通谕在与各宗教团体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沟通上,已迈出良好的一步,那些气候活动人士对此必定表示欢迎。
新闻报道范围
与过去大部分的宗座通谕相比,《愿祢受赞颂》受到教内外新闻界更广泛的报道。就如前面提到的,这道文献的普及由一个记者招待会开始,这为一道宗座通谕来说是不寻常的。格雷戈·易兰桑(Greg Erlandson)和格雷臣·克洛维(Gretchen R. Crowe)两人在回顾美国天主教2015年的重点报道时,考虑到气候问题在美国的极富争议性,以及美国教内外新闻界保守派评论人士因这道通谕而引起的对教宗方济各的种种批评,而把《愿祢受赞颂》列为发行重要性排榜上的首位。这两位研究学者正面评估梵蒂冈的传播活动说:“梵蒂冈很周全地设想公布这道通谕的传播策略,这项公布出现在许多媒体管道上,与通谕所要传达的讯息配合一致。这扩大了教宗讯息的影响力,使之超越宗座文献惯常的读者群”[4]。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道通谕在宗座诸文献中也发生空前的意外:梵蒂冈是“泄露消息” 的受害者,因为有位记者违反新闻发布时限禁令,在文献正式公布前三天便为文透露内容。按照常规,梵蒂冈会事先把将要公布的文件交给派驻梵蒂冈的新闻记者,让他们有充分时间妥善准备要撰写的文稿;但接获文件的记者们也得信守规定,在特定时限之前不得发布消息。玛莉卡·斯帕雷塔(Marica Spalletta)写道:“在意大利周刊L’Espresso 网站上集中讨论一项非常重要的破坏宗教消息时限禁令的事件:在正式公布教宗方济各《愿祢受赞颂》通谕前三天却外流出文献草稿。这项泄露消息事件很令梵蒂冈官员厌恶,他们指称此举乃‘不礼貌的行为’,同时吊销桑德罗·马吉斯特尔(Sandro Magister)这名泄露消息记者派驻梵蒂冈的执照”[5]。这事件没有影响意大利新闻界集中报道、谈论这份文献,在泄露消息之后连续七天,计出现103篇相关的报道,其中仅17篇涉及违规事件[6]。
在美国和英国,关心气候问题的非教会新闻界大都介绍这道通谕为“第无数次政治和社会性辩论(气候问题)的声音”。文献的宗教性层面大部分被忽略,或被归类到先已存在的“宗教类”档案中。“在教宗方济各之前,一般(非天主教)新闻媒体极少提到教会有关维护大自然的训导,即使《愿祢受赞颂》通谕在公布后,仍然没有被视为教会训导上的根本改变来介绍;它们仅将之视为政治性质文件来介绍”[7]。
传播的分析
传播研究学者一般运用原文分析(analisi testuale)、言论分析(analisi del discorso)、文辞分析(analisi retorica)、上下文关系分析(analisi contestuale)以及内容分析(analisi del contenuto)的研究方法来看《愿祢受赞颂》通谕。
原文分析系仔细阅读特定的传播产物,藉以辨识它的模式和仔细检视其内容。传播学者将这道通谕视为激发改变的因素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桥梁。此外,他们也注意到与先前的宗座文献相较之下,宗座机构对环境的认识有所进步。研究学者同样发现,这道通谕一如所有教宗文献的特征,也不乏引据教会其他文献的声明。
言论分析特别注意一份文献的多重语境,经常将之与其他类似文件及其结构相对照。研究学者本着这个方法来看这道通谕,他们提醒注意教宗所写的有关消耗(consumo)之事,并呼吁作为消耗者的人民对此负起更多的责任。其他的人则认为这道通谕乃是宗教性质的环境传播的典范。这类言论分析的良好范例可以在埃里克·卡斯特罗(Erik Castello) 及萨拉·杰苏阿托(Sara Gesuato)两人的著作中找到。这两位学者在这道通谕的结构中举出四个主要关键,即:环境,社会的相互作用,人性及神性。为了证明这个说法,他们举阿米塔夫·戈胥(Amitav Ghosh)的看法,将教宗通谕与2015年巴黎气候合约做对比说:“戈胥强调这两道文献谈论同样的问题,也引述相同的资料来源,然而通谕的用语和立场却非常不同。事实上,依他(戈胥)的看法,《愿祢受赞颂》通谕简单、适度、清楚,适合每位读者。通谕在对当前的现象、尤其对经济无限制地成长所做的公开批评、为绝大多数被排除在外的人类大众发声等方面,就凸显这点。整体而论,戈胥认为教宗这道通谕开放、直接,因为它从最普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内部来思考生态问题,并显示其对自由限度和人类能力有限的认识”[8]。
文辞分析从不同面向探讨文献,一般而论着重在词句和其意义上,也经常与别的文献做对比。在此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教宗方济各在文中表达的“我们共同的家园”(la nostra casa comune)的称呼便遇到不同类型的公众。其次,我们遇到的两个例子使教宗的通谕相似其他有关环境的著作。林奇(Lynch)根据美国宗教学者、自称为“地质学家”并致力于研究环境问题的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神父的著作[9],检视教宗的通谕。不论是教宗或是贝里神父都使用“完整生态学”(l’ecologia integrale)的基本隐喻,虽然方式不同却殊途同归。在注意到教宗和贝里写作的相似之后,林奇指出“贝里和教宗方济各两人对人类本位论(antropocentrismo)所主张的人乃宇宙中心的思想都持批评态度,但彼此立场不同,因为教宗也批评贝里所强调的地球为宇宙中心的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o)”[10]。此外,教宗强调伦理道德教育,而贝里则指出在各种媒体上以创意性从事学术教育的重要性;教宗以天主教圣传和圣经为他的通谕的基础,贝里则认为圣经只不过是天主启示的方式之一。
克雷格(Craig)提供一个与尤蒂特·布特勒(Judith Butler )和凯瑟琳·尤索夫(Kathryn Yusoff)两人的著作有关的文辞分析[11]。这两位作者把备受争论的人类世(或称人新世Antropocene)概念置于中心,而克雷格则“以为‘宇宙’这个名词阻止教宗方济各面对种族问题,也因此教宗在他的批判性讲话中,几乎见不到环境种族主义(razzismo ambientale)和种族不正义(ingiustizia razziale)”[12],然而布特勒和尤索夫却有力地辨认出这些问题。总之,对于克雷格而言,教宗方济各的《愿祢受赞颂》通谕提出拯救我们地球并解决生态不正义的热切呼吁,但他除了所写和所说的解决气候危机之道之外,对人类世观念有关结构上的种族主义的不同看法,在全球基督信徒面前却是一片沉默[13]。
非同寻常的是多米尼克·维金斯(Dominic Wilkins)的注意力特别聚焦在“视觉的诠释”(interpretazione visiva)上,而不太在乎教宗通谕的原文。他建议就梵蒂冈媒体和教宗祈祷全球网(Rete mondiale di preghiera del Papa)所制作的“照顾受造物”(Cura del creato)视频影片进行文辞分析。他写说:“‘照顾受造物’影片以希望的标记做结束,它极力避免足以令人感到无能为力的恐怖和罪恶感的情绪,但影片无力提供具体的步骤却令观众瘫痪,因为影片模糊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要求改变的声势”。维金斯继续说:“在宗教维护环境运动声势逐渐扩大的背景下,重要的是学者和艺术家该有挑选、甚至相反的的解决之道,这些途径能够激励每位以有关环境的文字或形象彼此影响的人,而在有人设法揭穿主流的说法时,这尤其显得特别重要。事实上,这部短片揭露欲有效地推翻绿色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老套是多么困难,就如这个实例揭示的,谁拟构这个思想就提出这个建议”[14]。
若瑟·宗佩蒂(Joseph Zompetti)也不赞同原文分析。他透过研究教宗方济各将罗马一座建筑物作为无家可归者住所的作为来检视“处所文辞”(retorica del luogo)的意义[15]。宗佩蒂“处所文辞”的议题接近教宗的行动和他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的声明。宗佩蒂的文章邀请聆听教宗的话并参与他的行动的人 “在面对某种操控的层级时,注意到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地位性质’,以及我们所占的地方。我们按照自己能力所及行事是合理的;必要时努力投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做是义不容辞的”[16]。
文辞轮廓(cornice retorica)分析是从外界其他的诠释角度来看一道文献如何组织它的建构要素。赫希·格雷念迪克(Hathi Groenendyk)自问教宗如何能够向在气候变化和信仰系统问题上意见如此分歧的世界讲话[17]。他的结论是:教宗使用亚西西圣方济各有力的“家庭隐喻”。至于文辞上的强有力,通谕的家庭轮廓引发两个挑战:“第一个是教宗方济各在通谕第90节有意肯定人类的独特性(unicità),但这就有损‘家庭’的概念…。第二个涉及家庭隐喻问题,它关系到天主教会内部性别平等的问题”[18] 。
其他有关通谕上下文的研究都着重在美国的状况,包括新闻界,有时也触及美国天主教徒透过本国政治分歧的眼光来看教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若瑟·布雷尼(Joseph Blaney)指出:虽然非教会新闻界都先入为主,以政治辩论角度来定位问题;但美国教会刊物,不论是保守派或自由派的,还是宁愿以牧灵而非政治立场来正视。这可以从读者在教内外网路新闻上所发表的评论得到印证,这些评论显示阅读教会新闻的人更乐于阅读宗教或牧灵内容的文章[19]。
由于教宗方济各在他的通谕中提到不同的传播媒体,所以有些学者以媒体生态分析来看通谕。他们认为从事类似的研究需要遵守并了解传播乃属知识和技术领域,它影响物理领域并形塑人们的意见。也因此,媒体本身对气候危机负有某种责任。布莱恩·基尔克莱斯特(Brian Gilchrist)为此举例,他把教宗对科技政治(tecnocratico)治理环境的担忧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科技的评判做了对比并结论说:“教宗方济各以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排拒科技政治的模式,因为他了解在一个致力于社会改变的团体内,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交叉作用的做法会比由下而上的做法更有可能导致模式的改变,因为后者信赖个别的人”[20]。其他的学者则提醒注意媒体生态与环境生态两者的相似,他们赞同教宗通谕中推动相关的教育的邀请。
至于内容分析,它引领读者深入研读作品,发掘其中的议题和问题。学者们使用这个方法来检视通谕所含的“伦理道德讯息”,列出一些如修好、损害及相互性等议题。另有一些学者则运用类似的做法来回应通谕,他们的回应发表在全球一些讨论族群的在线网路上。
传播界的回应
传播界学者们提出不同的方式,认为传播学院(le facoltà di Comunicazione)应该可以藉此回应教宗倡导完整生态学(ecologia integrale)的呼吁,这些方式包括媒体计划及教育方案。这些计划和方案除了使用社交媒体之外,也为促进不同族群就环境问题展开对话。
媒体与教育。《愿祢受赞颂》通谕第六章专事谈论“教育与生态灵修”,并期望从多方面展开行动。玛利亚·罗卡( Maria Roca)和彼得·柯克兰( Peter Corcoran),安东尼奥·赫利奥·浑杰拉( Antonio Hélio Junqueira) 和彼得·瓦伯乐( Peter Walpole)提及在三大洲经由媒体促进个人社会化的计划,为人们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服务[21]。他们建议使用媒体,经常提示因气候导致本地自然灾难的现象,藉以教导人们注意消费、生态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问题。他们意在帮助人们认识“新的生活风格”和新的消费方式。
专长于传播事业的圣保禄孝女会(le Paoline)修女发起一项创举,名为“怜惜与传播证书,媒体专业青年《愿祢受赞颂》全球社团计划”(Certificate in Compassion and Communications, a «Laudato Si’» Global Fellowship Programme for Young Media Professionals)。这是一种“怜惜与传播”文凭,它为媒体专业青年安排一个全球性研习《愿祢受赞颂》通谕奖学金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使传播界专业青年关心今日地球必须面对的关键性挑战,以便拟定照顾我们共同家园的行动策略”[22]。天主教国际媒体从业者组织(Signis)也筹办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研习活动,吸引了来自意大利、印度、菲律宾、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同业者参与。
对话。彼得·瓦伯乐举出几个对话的例子,特别是有关科学和可持续性(valori sostenibilità)的对话;林赛·克拉克森(Lyndsay Clarkson)则祝望在心理分析研究和环境研究之间进行这种对话;林内·雅布隆斯基(Leanne Jablonski)谈及科学研究者与信仰团体就环境问题进行对话,并给这方面的专家清楚指出一些已敞开的以《愿祢受赞颂》通谕为方向的道路;亚德纳内·莫克拉尼(Adnane Mokrani)则与伊斯兰展开对话,检视“伊斯兰宗教根据可兰经、伊斯兰传统教规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的观点,对生态所持的神学与神修原则,进而发现《愿祢受赞颂》通谕是与伊斯兰对话的依据”[23]。以上这些研究具体回应了通谕第五章的邀请,在不同的族群中做对比,特别是在国际团体中就环境问题进行对话。
许多人敦促从神学角度进行对话。德尔莫特·廉(Dermot Lane)提出神学与生态学进行对话,以便探寻教宗方济各使用“完整生态学”所表达的各种意义。恩格吉·伊贺纳卓(Ngozi Iheanacho)从神学角度认为应该承认女性在所有这些对话中的地位。她以尼日利亚妇女的观点使用生态女性主义(ecofemminista)神学的观念。安东尼·凯利(Anthony Kelly)也建议从教宗通谕的每一章找出一些提示,以便与这道通谕进行神学对话。他提议成立“一个让科学、艺术、人文科学、神学和神修学都参与的全方位交谈”[24]。
社会传播媒体。《愿祢受赞颂》通谕第一章就谈及社会传播,文中提醒人们注意今日新的媒体体系对社会内聚力及平等构成的挑战。马丁·卡巴何·努涅斯(Martin Carbajo Nuñez)评论这件明显的事时,强调社会传播的商业逻辑足以造成“精神和媒体污染”,展示新的人际关系,把人从自然中孤立起来[25]。马尔切罗·瑟梅拉罗(Marcello Semeraro)和奎多·吉利(Guido Gili)从环境传播和社会传播两方面检视教宗通谕,他们强调“照顾大自然环境和人类也表现在建立并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传播环境”[26]。
通谕的影响
传播学者衡量了教宗通谕对读者、教会团体以及政治产生的作用。某些学者使用读者在不同网路线上交谈中所发表的评论为一般性准则,来衡量读者对通谕的兴趣;另一些学者则从堂区或教区小组特定的讨论来观察通谕产生的影响;再有部分学者则从一些研讨会、大学和气候运动人士在相关活动中引述通谕的消息来分析这件事。一般而论,这些相关的研究都指出,人们以地方性的感受和看法回应通谕,也就是说他们的回应都与其所属的地区如非洲、亚洲、美国或他们的教区的特定情况有关。
艾斯利·莲德伦(Ashley Landrum)和罗莎琳·巴斯克斯( Rosalynn Vasquez)两人检视来自美国的资料后,发现人们对通谕的接受都与他们所谓的“方济各效应”(Francis effect)有关,也就是他们回应的对象是教宗本人,因为教宗影响他们以积极或消极的态度来评估气候讯息[27]。马尔孔·马克凯伦(Malcolm McCallum)领导的一项对各国回应教宗通谕的研究发现,对环境问题更具关心和兴趣的公众“特别是在天主教国家。而发达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之间也有重大的差别”。此外他也观察到“《愿祢受赞颂》通谕颁布两年后,天主教会展开了一项长期可持续性(sostenibilità)的计划,这项计划可能演变成一个大型的天主教环境运动”[28]。
有些传播研究学者也因策略传播(comunicazione strategica)之名,也就是为了推动某特别目的而利用广告、宣传消息或公共关系这类传播,而接受《愿祢受赞颂》通谕。在通谕颁布后短短几年内,研究学者便建议将通谕应用在环境权利(diritto ambientale)上[29]。托马斯·克莱恩(Thomas Klein)与金尼·拉斯尼亚克(Gene Laczniak)两人采用销售学(marketing)传播的看法,把教宗通谕定义为是为合理与可持续性的环境所做的巨型销售学广告(manifesto)。为他们来说,这道文献为受尊重的环境销售学提供伦理规范[30]。与此类似的是一些管理传播(comunicazione manageriale)的学者也建议《愿祢受赞颂》通谕提供更好的、可行的管理理由,以便减少废物,增进对人、对文化改变和对人际关系的关怀[31]。
结论
从我们上面所谈的呈现出一些议题:尚无法为通谕定位,研究通谕的动机,以及研究者使用什么工具进行研究。关于第一点,美国新闻界一般把通谕引入美国政治和人为气候变化的争论中,而忽略通谕的本质及其宗教背景。学术界对通谕的看法似乎也一样。除了宗教性作家或那些从神学角度谈论通谕的传播面向者之外,学术界研究人士的分析都视教宗的通谕为一项独立存在的声明。他们中许多人暴露自己对天主教有关环境的社会训导缺乏认识,他们以为教宗方济各的通谕是个突然的转变,而不是教会数十年来对地方和国际教导的极致。毫无疑问,天主教由于缺乏传播,对这些议题和相应的教导策略相当有限,所以对这一切也负有部分责任。
第二点,一些学术界写的有关《愿祢受赞颂》通谕的文字反映出作者们重视通谕所触及的议题甚于通谕本身。许多发表的文章把通谕与已经在不同事件上或在杂志专刊上讨论过的议题连结在一起。虽然这样的做法亦属寻常,然而某些文章却惊讶为什么教宗或教会对这类问题表示重视;其他一些来自宗教界新闻的文章则对通谕表示满意,因为这道文献重视伦理道德问题。
至于第三点,传播研究工具经由讨论通谕而进入这道文献的本质问题。即使某些研究学者建议把通谕与其他有关环境的文章作对比,但这些工具在分析通谕后仍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通谕本身。那些比较倾向于把视线伸展到通谕以外的人士发现通谕内有关于环境传播、策略传播或媒体生态学的实例,于是设法指出通谕是如何地能够影响社会大众的言论或改变人们的态度。
《愿祢受赞颂》通谕乃是研究教会传播的可能性以及教会在全球严峻危机中发出伦理道德声音的可能性的有趣实例。对学术界人士来说,这道通谕乃是邀请他们进行包容和持续的对话的第一步。
- 关于这道通谕获得的接纳和产生的影响,最好是留意教宗方济各最近发表的《请赞颂天主》(Laudate Deum)宗座劝谕,本《公教文明》将在下期予以分析。 ↑
-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可参见P. A. Soukup,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bout Laudato si’»,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42 (2023/2) 4-20. ↑
- G. Marshall, «Communicating with Religious Communities o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Overview and Emergent Narratives», in Journal of Interreligious Studies 19 (2016) 27. ↑
- G. Erlandson – G. R. Crowe, «Church communication highlights 2015», in Churc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1 (2016/1) 9-10. ↑
- M. Spalletta – L. Ugolini, «From Trustee Journalism to Embedded Journalism: The News Embargo Break of Pope Francis “Laudato si’”», in Revista Romana de Jurnalism si Comunicare – Romanian 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11 (2016) 17. ↑
- 参见同上,18。 ↑
- M.-J. Pou-Amérigo, «Framing “Green Pope” Francis: newspaper coverage of Encyclical “Laudato Si’”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Churc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3 (2018/2) 148. ↑
- E. Castello – S. Gesuato, «Pope Francis’s “Laudato sì’”: A corpus study of environmental and religious discourse», in Lingue e Linguaggi 29 (2019) 123. 书中提及 A. Ghosh, 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
- 参见C. O. Lynch, «Relig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rhetoric of Thomas Berry and Pope Francis»,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n 45 (2022) 111-129. ↑
- 同上,117. ↑
- B. B. Craig, «Restaging the anthropocene: “Laudato si’” and the rhetorical politics of the universal»,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n 44 (2021/2) 33-46. ↑
- 同上,33。 ↑
- 同上,44。 ↑
- D. Wilkins, «Pope Francis, Care for Creation, and Catholic Environmental Imager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25 (2020) 369 s. ↑
- 参见J. P. Zompetti, «The Palazzo Migliori as Exemplification of “Laudato Si’”: The Rhetoric of Place/Space»,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n 45 (2022/2) 57-68. ↑
- 同上,66。 ↑
- 参见K. Groenendyk, «Creation as Sister, Brother, and Mother: Familial Metaphors as a Frame for Climate Change Action», ivi 44 (2021/2) 47-56. ↑
- 同上,53s。 ↑
- 参见J. R. Blaney, «A World Grappling with Pope Francis: “Laudato si’” and the Contested Frames of a Secular-minded Church», ivi 44 (2021/2) 6-15. ↑
- B. Gilchrist, «Papal Media Ecology: “Laudato Si’” as a Medium of Technocratic Resistance», ivi 40 (2017/1) 56 s. ↑
- 参见M. F. L. Roca – P. B. Corcoran, «Ecology Meets Integral Ecology Meets Media Ecology: Education for “Laudato Si’”», ivi 44 (2021) 69-84; A. Hélio Junqueira, «A Igreja entra no clima: comunicação, educação e consumo em “Sobre o cuidado da casa comum”. Encíclica papal de Francisco», in Comunicação, Mídia e Consumo 15 (2018) 186-203; P. Walpole, «Jesuits from Asia-Pacific in the Time of “Laudato si’”: Reconciliation with Creation», in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3 (2016) 593-618. ↑
- Daughters of St. Paul圣保禄孝女会, «“Laudato Si’” and communications», 2020 (www.paoline.org/site/laudato-si-and-communications/?lang=en). ↑
- 参见L. L. Clarkson, «Our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ural World. Review of Engaging with Climate Change: Psychoanalyt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5 (2017/3) 537-553; L. M. Jablonski, «Scientists and faith communities in dialogue: Finding common ground to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in AGU Fall Meeting Abstracts, 2017; A. Mokrani, «Islamic Ecological Reflections in Dialogue with “Laudato Si’”», in Islamochristiana 43 (2017) 115-122. ↑
- D. A. Lane, Theology and Ecology in Dialogue: The Wisdom of» Laudato Si’«, Dublin, Messenger, 2020; N. N. Iheanacho, »The place of women in “Laudato si’”: The Nigerian reflection«, in Journal of Gender and Power 5 (2016/1) 29-46; A. J. Kelly, »Laudato Si’«: An Integral ecology and the Catholic Vision, Australia, ATF Press, 2016. ↑
- 参见 M. Carbajo Núñez,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l ecology in the encyclical Laudato si’», in Redemptorists Scala News, 7 ottobre 2022. ↑
- M. Semeraro – G. Gili, «L’ecologia della comunicazione e dei media nell’Enciclica “Laudato si’”», in Problemi dell’informazione 41 (2016) 253. ↑
- 参见A. R. Landrum – R. Vasquez, «Polarized U.S. publics, Pope Francis, and climate change: Reviewing the studies and data collected around the 2015 Papal Encyclical», in WIREs Climate Change 11 (2020) e674. ↑
- M. L. McCallum, «Perspective: Global country-by-country response of public interest in the environment to the papal encyclical, “Laudato si’”», i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 235, 2019, 209-225. ↑
- 参见K. P. M. Cabatbat – T. M. Camarines, «Analysis of the writ of continuing mandamus in the light of “Laudato Si’”», 11th DLSU Arts Congress At DLSU, Manila 2020; L. A. Silecchia, «Conflicts and “Laudato Si’”», in Journal of Land Use & Environmental Law 33 (2017/1) 61-86. ↑
- 参见T. A. Klein – G. R. Laczniak, «“Laudato si’” – A Macromarketing Manifesto for a just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in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41 (2021/1) 75-87. ↑
- 参见 M. J. Urick – W. J. Hisker – J. L. Godwin, «Management Response to “Laudato si’”: An Operational Excellence Perspective», in Journal of Biblical Integration in Business 20 (2017/2) 2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