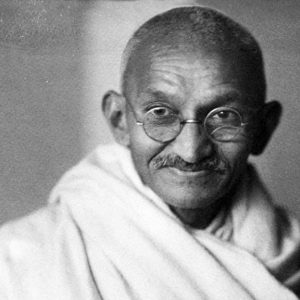亚当·斯密(1723-1790年)首先以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家而著称于世,但实际上,他的贡献也表现在哲学方面,尤其是道德哲学[1]。他将自由竞争理论视为提高国家质量及财富的必要条件,并因此而被赞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这一信念扎根于他的生平经历。在牛津学院学习期间,斯密因其低下的学术质量而感到失望,他发现这所学院无法与他早年就读的苏格兰大学媲美。斯密认为,这是由于支付给英国学院教授的薪金既不取决于其教学质量,也不考虑他们是否能够激发学生的热情。
亚当·斯密的传记也揭示了他极其丰富多彩的教育之路:他的学术生涯始于修辞学和道德哲学教授之职,在从事天文学和语言起源研究之后才投身于经济学。斯密的人生轨迹也体现于他生前仅有的两部著作的出版日期:《道德情操论》(1759年)的问世早于其成名作《国富论》(1776年)近二十年,而且取得了同样的成功,至斯密去世时已出版了六版。
斯密对经济学的兴趣早已表现于格拉斯哥大学的课程中,在其《道德情操论》的热忱读者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先后任命他为家庭教师及爱丁堡市海关专员后,这一兴趣更是大为提高。这不仅为斯密提供了充足可靠的经济来源,也使他有机会周游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他在法国接触到了《百科全书》(Enciclopedia)的主要人物,尤其是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Voltaire)、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ond d’Alambert)以及理学理论家魁奈(François Quesnay)和杜尔哥(Jacques Turgot)。至于意大利,他曾与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安东尼奥·热诺维西(Antonio Genovesi)神父以及著名论述《货币》(Della moneta,1751年)的作者费尔迪南多·加里亚尼(Ferdinando Galiani)神父有所交往,这两位神父都是修道院院长。
《道德情操论》
接任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在格拉斯哥的道德哲学教席之后,斯密最初一边与休谟的怀疑论观点进行比较,一边在更严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新的阐述。他继续探讨两者对感情作为行动评价标准的重要性。对此,其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标题便是最好的印证。在这部著作中,情操和想象力与经验相统一,而经验的保障则寄托于一个概念(天主),这个概念能够为休谟所警告的种种疑惑和无序的圈套提供答案,并对由于永远无法确认事物现状的绝望而导致的最终结果进行补救[2]。在斯密看来,对天主的信仰也同时满足人们对正义的需求,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这种需求在生活事件的因果链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回应。
斯密认为,行为的基本标准不能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推导出来,而要从直接经验中确定,这要归功于常识,而哲学的任务正是培养常识(参见Teoria dei sentimenti morali, p. VII, sez. IV, cap. 14)。这位苏格兰哲学家认为牛顿的科学是理解人类行为的最适当的研究方法,他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假设,即:“本性在这种情况下与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一样,以最严格的节约方式行事,从同一个原因产生多种效果”(p. VII, sez. III, cap. 3, §3)。这一选择使他与笛卡尔人类学保持距离,笛卡尔人类学的特点是唯我论和理性情感二元论;在斯密看来,两者皆有助于认识道德行为可能的正确性。事实上,对经验的分析表明了情感在道德中的重要性:一个人只有“意识到被爱”(第I页,第二节,第5章)才会感到幸福,才能为实现他人的利益做出贡献。理性不可能为人的行为提供无可指摘的指示;它可以制定一个事物的概念,却无法界定其可爱或可恶的特征(参见p. VII, sez. III, cap. 2, §7)。
最重要的是,感情是使人能够在与他人对比之下而认识自我的途径。斯密认为,共情(simpatia)是道德判断的普遍原因;通过共情,人具有借助于想象而走出自我、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无论一个人认为自己多么自利,在他的天性中都显然存在着某些原则,而这些原则使其参与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尽管他从他人的幸福中除了因此而感到快乐之外一无所获。爱和怜悯就是这样一种情感,当我们看到他人的悲惨遭遇或是被引导着设身处地想象这种悲惨遭遇时,我们就会产生这种情感[…]。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或者最顽固的侵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完全没有这些情感[…]。爱和怜悯是表示我们分担他人痛苦的恰当词语。共情这个词,虽然最初的含义可能是与此相同的,但现在可以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感情的参与感,而不会显得过于不当”(p. I, sez. I, cap. 1, §§1.5)。通往善的道路是内省的心理旅程,它使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事物能够得到确实的认可。
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具有结构性的向他人开放;然而,这种道德体验的感情方式表现出一种极端的不对称:人既会对微小的喜悦也会对最强烈的痛苦产生极大的共情。由此,道德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五光十色的迷惑,比如夸张的消费主义: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只注重外观,希望获得价值和尊严,而这些是它们其实根本不具备的品质。这种囤积物品倾向背后的动机正是出于一种情感;与其相关的因素并不是生活得更好的愿望(这几乎总是难以实现的),而是对他人看法的顾虑:“这个世界上所有劳作和辛苦的目的是什么?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统治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为了满足自然需求吗?[…]难道他们认为在宫殿里比在茅屋里胃口更好,睡得更沉?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恰恰与此相反的情况,没有人会忽视这一点。那么,贯穿人类各个阶层的效仿行为从何而来呢?我们将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称为人类生活的伟大目标,这一提法的好处又是什么呢?被观察到、得到关注以及赢得共情、恭维和赞许,这些都是由此而产生的好处。我们所关心的是虚荣,而不是幸福或快乐”(p. I, sez. III, cap. 2, §1)。
这是一个对时尚现象的仔细分析;效仿的推力实际上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广告和商业的基础,而技术和工业革命则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动力:“有成就”意味着拥有某些财务或是以某种方式展示自己,从而被视为应受尊敬的人。但是,人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个人、其价值观及活动,不如说更是正如斯密所指出的,是对那些似乎有钱有势的名流趋炎附势。缺少教化的想象力会使人选择自己实际上并不希望的东西,人们效仿某种东西只是因为看到它在别人身上的实现,而不是出于对它本身的注重[3]。
根据对生活的经验主义态度,斯密深信对物理对象的错误感知与道德领域的错误判断如出一辙;因此,哲学中固有的批判性反思非常重要,因为“习惯与经验教会我们轻松自如以至几乎无意识地去做这些事”(p. III, cap. 3, §3)。在这位苏格兰哲学家看来,这种对自发性的纠正是可能的,也是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这要归功于被他命名为“公正的旁观者”的贡献,这一称谓后来广为人知,“他是一个完全坦率而公正的人,与我们没有特殊的关系[…]他既不是父亲也不是兄弟,而只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他对我们的行为不偏不倚,就像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一样”(p. III, cap. 2, §31, n. 27)。公正的旁观者通过对不同观点的思考和比较而形成,他能够对形势做出正确的评估,达到一种对自我及他人超然的看法(p. III, cap. 1, §6)。
斯密深信各方达成这种协议的可能性,因为公正的旁观者是一种“预设的和谐”,是天主圣意的运作:这种仁慈的天主圣意能够将每个人的倾向引入一种普遍的秩序之中(参见p. VII, sez. II, cap. III)。事实上,共情是“无形之手”存在的标志;它使人能够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为自己和他人确定可能的最佳利益。
《国富论》
在其成名作《国富论》(1776 年)一书中,斯密进一步将他对预设结构性和谐的信念应用于经济学中。初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只是谋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及对他人利益的影响,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个人的自利心会对社会财富作出贡献:“我们期望的餐食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祈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自爱];我们向来不与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对他们的好处”(La ricchezza delle nazioni, l. I, cap. II)。事实上,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也是“无形之手”在发挥作用,它能够在个体无意识的情况下将其自利心引向更崇高的目的:“裁缝并不想做他自己的鞋子,而是从鞋匠那里购买。鞋匠并不想做他自己的衣服,而是雇裁缝去做。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生意全部集中到比邻人有优势的方面,并以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或以这些产品的价格的一部分–两者并无区别–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物品”(l. IV, cap. II)。
借用《百科全书》中的一句话,斯密深信经济学与物理学一样,都是自动运行的:“就像一个自动上发条的钟表”。商品的价值可以根据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以货币支付,而不是通过以物易物)而准确地计算出来,因此,这位苏格兰哲学家提出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理论,以便促进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参见l. I, cap. I)。他还认为,任何旨在调节市场的制度性干预都会损害市场的平衡,因为这会限制贸易自由并进而阻碍发展(l. IV, cap. IX)。斯密之所以持这种保留意见,与其说是与重农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有关,不如说是斯密认为当时的政府完全站在最富有者的利益一边,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政府不顾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利益,只为特定的贵族阶级提供特权,而在这位哲学家看来,资产阶级企业家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此框架内,主权者的作用必须仅限于三项任务:1)保护社会免受暴力和侵略;2)保护每一个体免受他人压迫;3)创建和维护公共工程,如果任由个人利益操纵,这些工程便不可能存在(同上)。
《国富论》被推认为现代经济学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因为它引述了大量的读物和经验,展现了广阔的视野,采用了旨在找出问题原因的方法论(即后来的作者广泛采用的所谓“病因学原理”),最重要的是,它的文笔思路清晰,质量上乘。劳动分工、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的质的区别、资本与利润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区别、供求规律、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等术语将在此后进入经济学家的词汇中,即使其中的一部分已曾被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和雅克·杜尔哥(Jacques Turgot)等早期作者所采用。
该书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众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均对其进行了研究和评论。第一版于出版后六个月即已售罄,在随后的十年间,另外四个版本又被相继推出。这部作品在英国得到了议会两党的广泛支持:保守党(托利党,Tories)认为该书证实了私有财产的自然性;自由党(辉格党,Wighs)则对它捍卫个人自由表示赞扬。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和斯图亚特·米尔(Stuart Mill)认为,它证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否定了国家干预的合法性。然而,其他人(巴特勒、门德维尔、马尔萨斯[Butler, Mendeville, Malthus])则强烈批判了这种相信天佑的秩序能够保证人人富足的观点。在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布伦塔诺、马克思[Hildebrand, Knies, Brentano, Marx])在提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的同时指出:亚当·斯密的建议具有双重灵魂,即道德上的利他主义和经济上的自利心;缺乏制度控制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导致日益严重的异化。
两部相互对立的作品?
尽管那些尤其涌现于德国的反对意见,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斯密之两部著作中所显示的相同点多于不同点[4]。初看起来,这两部著作似乎描绘了截然不同的视野:《道德情操论》是关于共情和关心他人,而《国富论》则展示了一个在“无形之手”严格操纵下由非个人规律和机械规律(商品价值的计算、利润率、供求趋势)所支配的社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表述在这两部著作以及另一部在其死后出版的《天文学史》中反复出现:虽然著作不同,但在一个方面却是一致的:它们以相当客观和贬低的方式展示了与人这一更大维度的关系。在天文学中,“无形之手”指的是原始人的迷信,他们将自然现象的解释归因于木星的作用,而不是诉诸理性;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中,“无形之手”指的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愚弄”,使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反倒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这一机械论性质符合牛顿机械论对世界及人类的看法。
《道德情操论》以希望再写一部关于生活的社会和法律方面的著作告终:这部《国富论》的确于17年后问世了。即使对共情作为一种能够领悟对方感受从而使双方受益的基本态度这一描述,也似乎与上文所提到的酿酒师和屠夫的例子并无太大差异。
关于“共情”(simpatia)这一概念是否可以追溯到“同理心”(empatia),人们一直对此争论不休;但有趣的是,人有一种自然的生物倾向,即理解他人的经历和感受并参与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后来科学研究所发现的镜像神经元,即在我们的大脑结构本身内所发现的社会性和利他主义的生物倾向[5]。
斯密是一位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深信自己已经在牛顿的科学发现中找到了解决当时大多数问题的可能途径,他试图在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确立准则,以摆脱他的同事、朋友及导师休谟在哲学上所陷入的怀疑主义迷途。为了证明其合理性,他诉诸于“无形之手”这一备受争议但却十分重要的概念。“无形之手”是 “天主圣意” 介入人类历史的一种方式,一方面能够调和自利心的激情与幸福,另一方面能够为市场经济提供科学依据。
然而,他并没有掩饰这项事业的艰难。他认识到,被爱的愿望与生活中不可预见的事件(反复无常、难以预测的“命运”)相冲突,而这些事件“很少有助于幸福”(Teoria dei sentimenti morali, p. I, sez. II, cap. 5)。在《道德情操论》第二版(1761年)中,“公正的旁观者”被视为道德判断正确性的保证,但在第六版(1790年)中,这一作用被彻底重新评价,因为它不能免于不道德和无序的激情,例如社会习惯与时尚[6]。公正的旁观者若想名副其实,就应该是人性创造者的成果(道德家称之为“自然法”,是永恒法则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以往经验的总结:因历史悲剧而产生的恐怖感就表明,道德判断不可能是社会习惯或当时历史状况的产物。斯密自己也认识到,决疑法不能建立道德基础,而是需要根据美德行事的能力(参见Teoria dei sentimenti morali, p. VI, sez. III, cap. 3, §1)。
即使在经济学领域,斯密也清楚地注意到因生产增长而带来的一系列有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尽管其思想中充满乐观主义,但在他看来,发展进步并不是自动且不可阻挡的,而不完善和局限性的持续存在则是科学方法永远无法彻底消除的障碍。如果说在《国富论》第一卷中,他认为分工可能为所有人带来好处,那么在第五卷中,他则进一步申确,分工也是工人异化和丧失理性的根源[7];最重要的是,不断增长的财富并不一定是面向所有人的利益,而是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一小撮不择手段的人手中(参见La ricchezza delle nazioni, l. IV, cap. XI)。继斯密之后, 这些主题由其他学者继续进行探讨,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黑暗面。斯密希望国家纠正这种状况(参见l. V, cap. I, art. II),尽管他也意识到这一愿望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很难实现:“似乎没有两个比君主和商人更不相容的角色”(l. V, cap. II)。在他看来,东印度公司事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如果没有制度的控制,自由市场不仅不会显示出“无形之手”的存在,反而会引发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上述多个方面的不可调和性清楚地彰显于斯密停留于草拟状态的政治理论,但是,为了保证自然自由(libertà naturale)能够遏制那些掌握市场最大份额之人的贪婪霸道,这种政治理论是不可或缺的[8]。
- 在他去世后,他的大多著述——大学执教时期的教学成果——被收录于The Works of Adam Smith, Zeller, Aalen, 1963,共5卷。其中包括:《道德情操论》(意文版:Teoria dei sentimenti morali, Milano, Rizzoli, 1995);《国富论》(意文版:La ricchezza delle nazioni, Milano, Mondadori, 2009);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
-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虚假的理性和毫无理性之间选择[…]。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如此大的迷宫,以至于不得不承认我既不知道如何纠正自己以前的观点,也不知道如何使它们保持一致”(D. Hume, Trattato sulla natura umana, in Id., Opere filosofiche, Bari, Laterza, 1987, vol. 1, 280/662)。 ↑
- “有些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的是在死后获得他们将无法享受的声誉。就在那一刻,他们的想象力所预见的是未来将赋予他们的名声。他们的耳边响起了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听到的掌声;这种对自己永远也享受不到的赞美的念头使他们内心坦然,抹去他们灵魂深处最深的自然恐惧,引导他们做出似乎完全超出人类本性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那种只有在我们无法再享受时才给予我们的赞许,或是那种根本没有给予我们、只有一但我们行为的真实境况得到世人的正确理解才会给予我们的赞许,这两个赞许之间肯定没有多大的区别”(Teoria dei sentimenti morali, p. III, cap. 2, §5; cfr p. IV, cap. 2, §9)。 ↑
- 参见P. Berlanda, «La simpatia e lo spettatore imparziale in Adam Smith: dalla filosofia morale alla filosofia della società civile», in Rivista di Storia Della Filosofia 37 (1982/1) 39-64; T. Raffaelli, La ricchezza delle nazioni. Introduzione alla lettura, Roma, Carocci, 2001; R. Faucci, Adam Smith: la vita, le opere, le principali interpretazioni. Lezioni introduttive, Pisa-Roma, I.E.P.I., 1996. ↑
- “人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动物,其生活依赖于理解他人在做什么、了解他人的意图和解读他人感受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人类就无法相互交流,更不用说创造社会共存的形式[…]。我们理解他人,是因为我们‘设身处地’,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境地,并‘模拟’如果自己真的处于这种境地会怎么做”(http://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neuroni-specchio)。参见G. Rizzolatti – L. Craighero, «The mirror-neuron system», in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7 (2004) 169-192. ↑
- “那些不幸在暴力、放荡、虚假和不公正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即使不能完全感觉到这种行为的不合宜性,也一定会感觉到它们可怕的邪恶及其应有的报复和惩罚”(p. V, cap. 2, §2)。 ↑
- “一个人若是终生都在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的效果也许总是一成不变或大同小异,他就不会有为克服从来不会出现的困难而瞑思苦想并因此而使自己的智力和创造力得到训炼的机会。因此,他会自然而然地失去这种锻炼的习惯并往往会变得愚昧无知,直至作为人可能达到的最愚昧无知的程度…由此看来,他在其特定工作领域内的技能以牺牲其智力、社交及军事素质为代价。然而,在每一个先进的文明社会中,这都是劳动穷人,也就是广大人民会必然陷入的状态,除非政府采取某种预防措施予以抵制”(La ricchezza delle nazioni, l. V, cap. I, p. III)。 ↑
- 参见S. Cremaschi, «Adam Smith. Sceptical Newtonianism, Disenchanted Republicanism, and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in M. Dascal – O. Gruengard (edd.), Knowledge and Politics: Cas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83-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