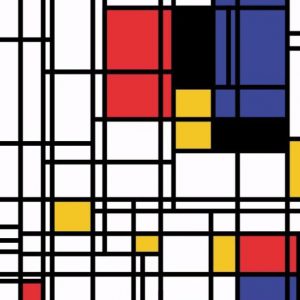为了能够如约履行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一届地球峰会的承诺,世界各国尽管拥有国家权力,但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峰会上提出的问题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中对接经济与生态,并由此奠定一块哲学基石:一种既不增加化石能源消耗又不增加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
在自然资源方面,且不谈全球变暖,当前体现这一囊括经济、社会、治理和生态需求难题的另一根本问题是水务的公共或私有化管理问题。2021年12月,《促进正义》(Promotio Iustitiae,耶稣会社会正义与生态秘书处刊物)以《水的呐喊和穷人的呐喊》为题向读者发出了警告。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水的呐喊“正是”穷人、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人的呐喊。
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为水所覆盖,其中97.2%是海洋咸水和一些来自地下含水层的咸水。淡水(占总数的2.8%)主要存在于南北两极的冰层中(占全球总水量的2.1%)。剩余的陆地可用水仅占总数0.7%,其总量估计在900,000至1,800,000立方公里之间,这一水源供全球居民使用,其中包括农作物(消耗70%的淡水)、工业(20%)和家庭用水(10%)。
不幸的是,可用水的分配极其不均衡。此外,含水层的年补给量低于12,000立方公里,而需求量的年增长率为1%[1]。根据不同的地区和气候情况,这将导致地下水位在2100年内下降50厘米至10米。总体趋势并不乐观:除了城市化发展、工业化以及取决于食品消费模式的农业种植及其需水量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地区长期饱受旱灾,包括中国、巴西、加拿大、摩洛哥、突尼斯、法国某些地区以及葡萄牙。近几个月以来,葡萄牙的水电站大坝已处于停滞状态。在澳大利亚、智利,甚至加利福尼亚,由含水层干涸而形成的干旱已造成放弃农场的现象。
出于以上原因,与那种相信地球拥有足够可饮用水的理论截然相反的事实是:无法获得饮用水的人口已超过10亿。在可用水资源之外,水的质量也同样是一个疑问。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包括气候、地质、储存、距离和取水时间等。此外,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忘记土壤侵蚀、环境退化及污染等悲剧。农业密集型地区存在着化肥带来的问题,其中特别是氮肥,这些化肥会导致水不能饮用[2]。此外,硝酸盐不仅有助于海岸上的绿藻繁殖,也使大气层在劫难逃,因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温室气体,更不要说能够促进微粒子产生的氨气。
砍伐森林的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联合国气候公约缔约国会议在2021年11月于格拉斯哥举行的年度会议(Cop26)上重新讨论了毁林问题(已被列入2020年议程)。近百个国家作出了停止砍伐森林的许诺,这在水循环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一承诺涉及世界上近85%的森林面积。合理砍伐的森林树木可以在后期重新生长,但我们这里谈论的并不是对森林的过度采伐,而是作为森林再生所必需的树种的灭绝而引起的森林地区不再生性。此外,造成森林不再生的原因还有道路、矿采、铁路、工业及行政区、城市化以至农业用地。某些国家必然会发现履行这些承诺的困难,尤其是巴西和刚果。
我们希望强调对森林的这一承诺,因为它具体凸显了教宗方济各所重视的整体生态学诉求。地球上森林面积的减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它始于近13000年前的谷物种植。谷物种植塑造了地球景观,导致森林消退,使人口增长与文明的双重发展相互渗透。
从近东的新月沃土到美洲的广袤土地种植着玉米,从拉丁美洲的藜麦到西藏的大麦,从非洲的大米到斯佩尔特小麦,从千穗谷到小麦,谷物促进了贸易、城市的萌生及帝国的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与象征性和技术性习俗以及孕育新生的蓬勃发展水乳相溶。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人类塑造了大自然,同时又在其实践、制度以及象征性和宗教表现中被大自然造就。
针对这种抹煞自然与文化间过度理智性划分的叙述,我们强调的一个事实是:符号并不具有某些人赋予它们的生态中立性。淡水不仅在地理上分布不均,而且也被滥用。让我们仅举两个例子。肉类消费既取决于社会地位的区别,也取决于饮食习惯,这于是垄断了可耕地的一个重要部分(试想用于喂养动物的高粱、大豆及玉米生产)。同样,让我们略谈一下对F1一级方程式赛车运动的热情。F1负责人在对展示了其效能的电能避而不谈的同时宣布了他们正在实行的生物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转向;他们为这种“100%生态化”(原文如此)的能源沾沾自喜,并已将其纳入F1规则。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生物燃料所需的种植与服务于肉类消费的畜牧养殖,它们大大增强了以牺牲森林为代价的农业用地和人类消费蔬菜作物生长的扩张,并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
如今,水务管理问题日渐紧迫。私人水务管理是否更为可取?还是应该托管于一个公共机构或是城市间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官僚主义、玩忽职守甚至腐败的风险。这是一个有趣的政治分辨议题。
国家职责
生命所必需的饮用水与未受污染的空气、清洁能源和生活空间一样,是属于每个人的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对于水这一公共资源,维也纳会议于1815年作出了关于欧洲河流(莱茵河、罗纳河、多瑙河等)的决定:任何国家不得以水坝或其他方式占有这些河水。这是一种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回归,它要求地方行政部门通过一种小运河网络管理制定水分配。这一将河水划为所有流经国家的公共资源的制度在亚洲一些地区得到了实施,但在中东却是另一番景象。
2022年2月20日,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erd)的头两台电力涡轮机被连接到电网上。这座大坝为非洲之最,长1.8公里,高145米,蓄水135亿立方米,耗资42亿美元。这座埃塞俄比亚自2011年开始规划的大坝落成于邻近苏丹边境的青尼罗河上,是尼罗河沿岸三个国家之间一个尚未解决的外交争端的起因。事实上,苏丹和埃及的数百万人口依赖于尼罗河水。关于这些争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首先收到了为此而提交的仲裁,而安理会则将其甩给了非洲联盟。具体结果尚无音讯。诚然,埃及与苏丹于1929年签署的一项议定书禁止后者在河上建坝,它们在1959年的另一协议授予埃及三分之二的尼罗河年流量。但是,埃塞俄比亚并非这些协议的缔约国,也因此从未受其约束。此外,尼罗河流域国家签署了一项新协议,它们不顾埃及和苏丹的意见,取消了埃及的否决权并允许开展水坝及灌溉项目。
水之所以被视为“公共资源”,是因为其供应属于国家职能。继蓝色社区(Blue Communities) [3]之后,联合国大会于2010年7月承认水是一项“基本人权”。两个月后,人权理事会通过了这一决议,并明确了各国在提供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义务。在此之前,一些国家已将饮用水权纳入了宪法,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乌拉圭、哥伦比亚、法国、荷兰王国、厄瓜多尔和比利时。归根结底,任何人都不应被剥夺这一权力。因此,水的私有化引起公愤。
水对于人民以及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海平面正在上升,甚至使整个地区被淹没,而湖泊和地下水位却正在下降。海平面的上升不仅源于两极冰川的融化,也由海水温度的上升而造成,这增加了盐水对沿海地区淡水的影响。在距斐济约500公里的图瓦卢群岛上,生活在那里的近12,000名居民因此而不再拥有可饮用水;现海拔高度为三米的基里巴斯也面临威胁。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延续下去,25年后的越南将会丧失10%的国土面积。
在其他地方,缺水应归咎于政治原因,例如在中东;然而,有时候,这也是由于因经济原因而引起的疏忽:这使我们想起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难以再生的咸海。
水的问题只会日益严重,因为即使考虑到生活标准以及农业和工业需求方面的改进,地球的可开发资源仍不足以满足预计在2100年将达到110亿的全球人口的需求。如果将所有用水量加起来,当前的水消费量为人均每天4000升,而约为12,000立方公里的自然地下水补给将无力满足这一需求,此外,从含水层中采水以及含水层补给分布非常不均,并因而导致悲剧性的沙漠扩大。
遏制沉沦
毋庸置疑,某些技术可以补给含水层:渗池、注水井、河道施工导流、雨水积蓄,更不用说生产饮用水的新技术:除海水淡化(但需消耗大量能源)外,还有改善卫生处理过程、开发冰山以及利用大气及云层中的水蒸气。但是,这些技术所要求的地质和气候条件仅允许它们作为解决水再生问题的辅助性手段。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领域,就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我们首先注意到公共当局的弊端:既缺乏明确的量化目标,也没有面对这一结构性挑战的相应手段。至今为止,监管似乎仍然不够充足。此外,越来越多的授权得到认可,其中一部分通过贿赂,这些授权准许某些作物使用超标的氮肥剂量(标准为每年每公顷170公斤)。
当然,许多建议可以有助于更好地调整施肥量,但各个国家并未对此作出明确承诺。有待改变的是耕作技术及农民在实践中的惯例:根据农业顾问的估计,出于人之常情,三分之二的农民倾向于过度施用氮肥。
地球上的水量是恒常的,但其质量却不尽相同。过去,大自然足以保证水的安全:土壤表层可以过滤废水,植物及其根部可以吸收几乎全部的污染物。而现在的情况已今非昔比:密集型农业将硝酸盐、磷酸盐和杀虫剂排放于土壤中;工业排放多氯联苯及其他染料;人类向环境中释放药物及洗涤剂的化学残留物:每个人都在行动中宛如水的主人,肆意使用、浪费或滥用。
如今,污染无疑得到了更好的管制。与普遍看法相反的是,西方农民已成功地为改进自然系统作出了巨大努力,这种自然系统基于一种限制氮肥及化学除草剂需求的生产模式。虽然是受管制所驱使,但他们也从中发现了自身收益。在专业农学家的建议下,废水现在可以通过种植精选草类的池塘系统得到净化,这是一些在农村地区经营的农业企业力所能及的。
尽管如此,特别是在城市化地区,废水净化必须通过沉淀池进行:为了消除病原体,必须使用或是化学产品——以往曾是次氯酸钠(俗称漂白剂),后来被氯气或臭氧取代——或是物理机制、紫外线以及超滤膜。这些除污染处理的耗资高于采水和运输水的费用,至少在排除通过蓄水池或第三和第四世界地区流动经销商分配水的情况下是这样。
占有水源
水资源管理及分配背后的一个棘手问题是水源及水资源私人所有权。对于地球上无数从自家水井或流淌在土地上的泉水中取水,甚至通过安装水泵从含水层中取水浇灌田地和花园的农民,我们应该如何归类?市政当局及地区[4]正在各地发起组织,以低于私营部门或市政公司经营的供水服务价格采水并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以便在更广泛的地区以更公平的形式分配水资源及相关成本。网络现象的矛盾性于此得到了无情的体现:一方面,它有助于那些网络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确与网络“相连”);另一方面,它排除受排斥的人群,这严重损害了在如此重要问题上理所应当的休戚与共。
无论是涉及河流、湖泊、含水层(地下水)、大气层还是云层中的水蒸气,但凡某些人的占有对其他人的所有形成限制,出于此类资源的全民享有性,一些疑问便会出现:从一块土地上涌出的水是否属于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就像大多数以瓶装形式销售的矿泉水水源?经过卫生处理的水属于公共机构还是卫生厂家?大坝的水属于大坝建设者、市政当局还是集水区群众?谁应该为漏水管道所浪费的饮用水买单?据估计,因国家而异,30%至50%的饮用水因供水系统的泄漏而被浪费。
这些隐藏的水资源占有问题是造成许多私有化败笔的起因。私有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经济严谨性名义之下的倡导,并同时经市政及国家当局(例如哥伦比亚)出于合理化和普及水分配网络的需求予以规划。私营公司或公共机构被授权使用以往属于当地社团的水源,并因而引起冲突,有时甚至导致严重的暴力事件,例如发生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血腥群众起义:他们虽然成功地驱除了一家私营特许公司,但安全水的分配并未得到保证。在更好的情况下,如在瑞士,国家法规将更普遍的利益置于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之上,比如市镇利益。
由于水的成本,经济学家从普遍权利的概念转向以他们更为熟悉的商品概念进行考虑。从这里到支持私人管理只有一步之遥,但需要作出分辨。饮用水被个人、小型团体或私人公司收购,成为一种由金融投机行为操纵的商品,使最贫困的人遭受最大的损害。
水分配的私有化
在占有水资源储备之外,水分配准许各种各样的私有化形式。如果规则欠佳,或者合同谈判中存在缺陷,甚至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如果受到某种腐败形式的影响,私有化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微妙的一点通常被私有化的反对者所忽视,那就是向私营公司提供的供水系统的退化状况:这些公司必须适时对其进行修缮。为此,将大多数水价上涨或水质下降的情况归咎于私有化管理的看法是一种误解。原因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即在不考虑腐败问题的情况下,这种价格上涨实际上是将以前没有进行的维护和投资费用重新纳入定价中。
由于水不再是免费的,各种具体问题随即接踵而来。谁应该支付水的运输和净化费用:是消费者,因为水有市场价值;还是纳税人,因为水是一种公共产品,就像以往从市镇中心的市政水泉中流出的水?谁应该管理水务及卫生设施网络:公共机构还是私营公司?在瑞士,水务管理主要由公共当局或主要由公共资本组成的公司承担。在法国,近75%的城市饮用水由三家大型私营公司管理:威立雅、苏伊士环境和索尔。
我们还必须谈谈瓶装水:法国达能和瑞士雀巢是雄踞世界市场之首并拥有多种品牌(依云、康泰克、圣佩莱格里诺、沃尔维克、佩里尔等等)的两家私营公司。目前,全世界每年售出近4700亿瓶水,而这个数字在半个世纪前仅为10亿瓶,这对含水层造成了巨大破坏(孚日地区的康泰克,中部高原的沃尔维克)。此外,瓶装水的输送同样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塑料对海洋的污染,更不要说运输生态。
管理和监督
支持还是反对水的私有化?相关的实例层出不穷,不一而足。必须检查的是每一项协议的内容:现有网络收购有没有适当规定?其租金?其维护?合同是否具备关于特许权目标及惩罚的明确规定?是否要建立一个储水库?是否需要提供基础设施及设备?水回收是否属于需要协商的一部分?在权衡公共、私人及混合型管理模式时,所有上述因素均需列入考虑范围。
诚然,公用事业单位受益于普遍低于私营部门的财务负债率,它们通常因此而能够降低投资成本。但是,这其中反映的事实只有一个:公共经营者失败的风险由纳税人集体担负,这不过是一个费用转移而已。一位反对私有化的活动人士表示:“在某些城市,私有化意味着削减服务,水质恶化的程度甚至达到不卫生、基础设施恶化以及玩忽职守”。这种情况尤其会在公共当局出于无能或在腐败的压力下签署单边合同时发生。政府官员往往会顺水推舟,天真地依附于特许公司的专业知识,而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监督和制裁系统。
“水务服务中不存在降低价格的竞争”:这一表述屡见不鲜,但需要我们加以斟酌。十几家国际公司分割了世界主要城市的巨大潜在市场。此外,它们仍面临国有化或被公共机构接管的威胁。比如,巴黎市于2010年从以前管理水务的公司手中接管了水务服务的特许权:威立雅负责塞纳河右岸的北部;苏伊士负责左岸的南部。当然,常识告诉我们:“每个家庭只有一根水管相连,这虽然并不完全属实,但水是必不可少、无可替代的”。但是,正如已经出现于天然气及电力输送领域的情况,无法阻止的是将网络维护委托于一家私营公司或公共机构,或者将供水及其收费委托于另一个与他机构竞争的公共或私营机构。
那些反对私有化的人不无道理地强调指出:“公共管理不含营利的需求”。然而,如果强调在利润减少的情况下,改进和寻求新的前进方向的动力也会减少,这个论点便会被驳倒。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私营部门缺乏透明度的问题。至于腐败问题,尽管它充斥于水务部门,但不幸的是,它并非仅属于私营部门的弊病。
技术官僚主义的回归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些被证明是诚实的市政及国家官员倾向于私人管理供水,甚至水源私有化?其原因是财务问题。如同政府移交高速公路特许权或转让机场或无线电频率一样,这些官员将私有化视为一种暂时修复财政或减少公共债务的方式,以延迟网络顺利运行的必要开支。总而言之,经济总会凯旋:因为无论如何,公民都是必要投资的买单者,要么通过税收,要么通过水费,否则就是网络退化。在我们的城市社会中,即使水源充足,也会产生运输成本以及更多的卫生成本,免费的饮用水已不复存在,就像没有免费的饭食。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由此,水务管理法规引起的争论显而易见。某些人谴责容许私有化的法规,政治领导人则矢口否认。每个选民都可以首先了解存在争议的法规之利弊,也可以了解这类问题的技术经济复杂性。然而,无论信息如何重要,都不会免除选民承担个人分辨的风险,这种分辨的依据是鼓舞他们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对最脆弱者(而不是多数人)的关怀:根据教会社会训导,这通常是基督信仰传统的特点。
这一领域内的公民态度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其表现是允许数据和技术经济分析作为政治选择的参考条件,但不完全取决于它们。这不仅是因为政治生活的基本标准在于合法性并不总是合理性的表达,而且因为每个选民所坚持的价值观导致不同的技术经济分析和选择。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技术官僚主义”,它以技术原因或经济业绩为借口,回避伦理道德及政治决择。在另一个具有类似生物影响的领域,新冠事件的例子说明,因研究状况及可支配卫生设备而宜的卫生技术制约因素对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至于经济可以无情地发号施令。
当今的教权主义
伴随着技术官僚主义的出现,另一种危险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并不足为奇、只是被当代资本主义翻版了的道德教权主义。这一危险体现于以经济当局的名义回避伦理道德及政治决策,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具备行动资格。经济权利并不优先于技术,更不用说优先于伦理道德,就像一个足球冠军并不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有能力决定是否将一个城市的水分配私有化。事实上,一切都取决于所追求的目标,这种目标制约着科学技术带来的限制。它首先取决于每个人所处的时间范畴,并最终由其生命意义决定:而这种意义又受每个人的个人旅程及其所经历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影响。这里面包含的仍是经济业绩与生态和社会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整体发展的挑战。
过去,教权主义关注的是“教士”,即那些自16世纪特利腾会议之后以罗马天主教司铎为原型的知识分子。某些人无视或假装无视那种效忠于资本主义技术主义的新式教权主义,仍将司铎视为主要攻击对象;他们并不提出对宗教的反对,而只是声称需要“提醒教会关注自身职责”。简而言之,正如第三共和国时期反教士者常说的那样,“司铎要呆在祭衣间!”。这意味着忘记了司铎也是公民,他们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享有良心自由并具有公开表达其宗教及道德观的能力。这也意味着如同技术官僚主义者一般,无视马克斯·韦伯所发现的经济、社会及宗教因素之间的相互渗透。无论以私人、社区还是公共模式解决水务管理这一重要问题,解决方案都离不开一个集体性、规范性和有约束力的管理机构,以符合费用直接承担者愿望的自主权来开展教会社会训导所要求的休戚与共,并同时尽可能控制含水层最大采水量。
- 含水层曾一度被称为“隔水层”,它不是地下水,而是含水的岩层。 ↑
- 我们知道,硝酸盐由大多数化肥中含有的氮经氧化生成,当它达到一定浓度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为50毫克/升)会导致水不能饮用。 ↑
- 蓝色社区是致力于控制和公平分配饮用水的公共社区联盟。该运动在本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并已延伸到世界各地。 ↑
- 区是市镇领土的一部分,如同在农村,村镇由合并在一起的若干部分组成。区在一些国家具有行政上认可的法人资格,比如在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