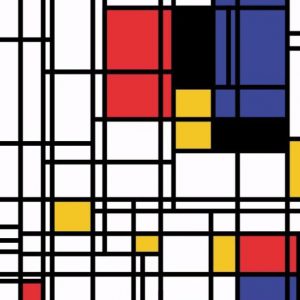友谊的艺术
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友谊被置于两个领域:一个可见于他所鲜为人知的私人轶事,另一个则置于他的心灵与作品的隐秘之所。他的最为知心的朋友之一——作为诗人与同胞的乔治·卡维蒂 (Jorge Calvetti),给出如下见证:“博尔赫斯无法在不感动自己的情况下谈论友谊…他的朋友,他的真正的朋友,都是在某些方面令他所景仰的…在他们的友谊萌芽之时,乔治·卡维蒂即有着让博尔赫斯景仰的力量” 1。
这一相互之间的景仰使得他们开始成为笔友:“许多次——卡维蒂说——我听到他带着颤动的声音说:‘当看到克鲁斯 (Cruz)去世时,我重重地跌倒了,即使闪电也无法令我如此震动’” 2。
友谊可以发生在现实中,也可以发生在想象中,如同博尔赫斯在阅读《堂吉诃德》后所得的结论:骑士堂吉诃德 (Don Chisciotte)与桑丘·潘沙(Sancio Panza)的友谊令人触动,其中不仅仅作者——塞万提斯(Cervantes) ——而且读者—— 博尔赫斯——二者均成为与角色之间的朋友。
文学与友谊之间的关系如此深厚,以致可映照永恒。博尔赫斯说,“冬尼 (Dunne) 3得出的结论是:在死亡中,我们将会理解永恒的幸福打开方式。转身回头,一生的点滴汇聚成为我们的喜悦之源。上主,我们的朋友以及莎士比亚将与我们合作。”4
《堂吉诃德》
为了深化主题,我们将博尔赫斯对于友谊的思考作为《曼查的堂吉诃德》(Don Chisciotte della Mancia)5的一个内在主题。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本西班牙和世界文学经典。从某种意义上说,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将经典定义为“一本从未说完它所要说的书”6,由于它被允许阅读和重读,所以历久弥新,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回顾塞万提斯的小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所带给读者的阅读与解释经验的沿革。
十七世纪,《堂吉诃德》被视为侠义英雄小说。西班牙贵族阿隆佐·奇夏亚诺(Alonso Chisciano)在如饥似渴地阅读骑士书籍后, 在他的忠实朋友桑丘·潘沙的陪伴下,开始了他的历险生涯。他渴望在面对各种不公之时行侠仗义,建树功名,以博取心上人杜奇乃阿(Dulcinea)的芳心。杜奇乃阿是一位粗野的农妇,却被游侠理想化。
如同小说在第二部分所呈现的,十九世纪弘扬与风车战斗的浪漫人士,对人物性格的关注超过冒险本身。阿隆佐·奇夏亚诺恢复了理智,却也随即面临生命之终结,由此谴责了使之陷入梦幻的骑士小说。然而,悖论性的是,这一转变亦将想象中的人物带上特殊的现实主义的色彩。
二十世纪,《堂吉诃德》的魅力在于其 “超小说”的特征, 由此开启 “元叙事”时代,在其中, 镜像游戏与叙事者的双重人格引导读者进入对于阅读经验的反省之中。
然而,在小说中,另一令人着迷且触动博尔赫斯的维度是, “在《堂吉诃德》中, 至少有两个着眼点:其一显而易见, 即富有想象力的贵族故事本身;另一则更为内在,或者也是更加真实的主题: 堂吉诃德与桑丘之间的友谊”7。
博尔赫斯继续补充道: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认为堂吉诃德是一个朋友, 但此种情况并非所有发生在所有的叙述人物中”。 8此外, 他继续谈论塞万提斯,这位阿根廷作家, 说,“与奎维多(Quevedo)不同, 对于他,没有人会感到他是朋友, 但不论是塞万提斯还是阿隆佐·奇夏亚诺,都让他感到亲如好友,并愿成为堂吉诃德,他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堂吉诃德” 9。博尔赫斯说,这是 “阅读旨要”, 而非 “概念性解释的旨要”。后者是一种抽象的视野, 而阅读始终是个人的和具体的, 一份与时间相关的经验: 阅读的时光以及再阅读的时光。
我们对于博尔赫斯的提问是: 作家如何创作一个能与任何一个读者交朋友的人物形象? 进而言之: 作家如何分享笔下人物的冒险经历的同时,成为使读者感到亲切的声音?
我们正在反思的是友谊,这一碰触内心深处的话题,以及它作为《堂吉诃德》的阅读关键,我们尝试朝此方向做一些延申,反思友谊是否可以成为每一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关键)。
友谊与信任
博尔赫斯说,也许, 《堂吉诃德》的有效性在于它的可信性; 这可以归功于被首先称为塞万提斯的 “声音”。那么, 声音如何能够比任何其他技术更能出奇制胜地唤起对人物的信任? 塞万提斯未具体回答, 但如此论述:对此问题的回答即对于一个“友善且自然的” 10声音的解释。于想象驰骋之中,作为读者的我们被卷入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友谊之中。 这一声音是有力的,因为它是叙述的 “称心工具”。如同塞万提斯想象中的作家塞德·哈梅特 (Cide Hamete)的笔,并由此成为《堂吉诃德》的尾声,当这支笔 (叙述者的声音) 说,“ 只是为了我,堂吉诃德才降临于世, 而我也只是为了他才存在。他知道如何活动, 我知道如何书写” 11。
这一声音并非强加于人, 而是为叙述的服务,使其更具亲切性。叙述者, 即这一声音, 与我们并肩, 并设法与我们的步伐同步, 成为志同道合之人, 而使自己消融于读者之中。在这个意义上, 他相信他的故事的价值,简而言之,为之见证。对人物的见证,胜于冒险。
这使得我们可以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加以区分 12。第一种类型最为简单,所表达的是一系列的冒险,如水手辛巴德 (Sindbad)。另一种类型是主人公通过一些事件来展示他的性格,如同《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分。第三种类型是主人公通过对环境的修正,也修正了自己的性格,如同《堂吉诃德》的第二部分。之于后者,某些情况下,主人公与自身的对话甚至可以极大地改变读者(以及作者)的现实!
博尔赫斯说,这正是堂吉诃德之死所带来的影响。在小说结尾的短短的一章中,主人公重新恢复了理智并回到了好人阿隆佐·奇夏亚诺的位置。如此动人,以致我们可以看到对作者塞万提斯的触动。“毫无疑问,博尔赫斯说,塞万提斯感到堂吉诃德之死是他自己的事情,一个令人悲伤至极的事件。读者为之哀伤,阿隆佐·奇夏亚诺也为之悲伤,将死之时他承认自己不是堂吉诃德。于此同时,塞万提斯同样为之悲鸣,于是,他用如下字句描述他的主人公之死:‘在在场的人们的哭泣与哀叹中,他交托了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说,灵魂已逝’。当此之时,我们期待一个文学性的句子:一个一举成名的句子,如同莎士比亚对于哈姆雷特之死的所流露的话语。然而,大相径庭之处在于,我们看到塞万提斯如此动容,以致在离开我们的朋友和他的朋友之时,他辗转反侧,最终以此结尾:‘他交托了他的灵魂’,并解释道,‘亦即,他死了’,由此避免了任何夸张的言辞。塞万提斯也随即陷入诚挚且至深的孤独之中” 13。
阿雷佐·奇夏亚诺之死将我们带回现实之中,宣告梦幻之结束。但悖论一般地,当我们已成为同情达理的奇夏亚诺的朋友,阿雷佐·奇夏亚诺所渴望成为的堂吉诃德,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看起来却似乎更为现实,也更为动人。
对博尔赫斯而言,在《堂吉诃德》中,“这些故事没有任何特殊性,在情节中看不到任何特殊的焦虑感,但从某种程度上,它们如同镜子,在这些镜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 14。因此,阿根廷作家立下如下原则:为了接受一本书,我们应当接受书中的主角。我们本应对于冒险充满兴趣,但是我们实则对于英雄更为关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信任堂吉诃德,尽管我们并不相信所发生的事件。此时,主角变得令人信赖并富于友爱,这正是塞万提斯令人景仰的伟大之处。
博尔赫斯由此批判那些将堂吉诃德和桑丘视为神话的观点。他说,一些学者 “停止认为他们是象征。但是,我的主张并非是为了攻击神话化的假设;即否定对于我们的朋友,这位西班牙人,畸形化的假设,认为他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神话中的桑丘和堂吉诃德可以是抽象的,但不是本书中的抽象,他们是非常独特和非常复杂的” 15 。
文学与幸福
博尔赫斯认为,相信堂吉诃德使人,对他的历险记感到满足、愉悦。1968年, 在用英语发表的关于奥斯汀(Austin)的演讲中,博尔赫斯说,“与堂吉诃德的相遇是他的生命中的关涉幸福的重要事件” 16。因此,对于塞万提斯而言,文学是娱乐的议题,想象一种未来的幸福,读者将会如同博尔赫斯一样获得幸福。
堂吉诃德在蒙特西诺斯(Montesinos)的山洞经历后,与桑丘谈论幸福。作为骑士的堂吉诃德被人用绳子捆绑并置于深渊一小时之长。此一小时的昏迷沉睡如同过了三天之久。除了对山洞隐喻的不可计数的阅读与解释 17,让我们继续关注桑丘的话:这一天他获得了许多的好处,“首先是我认识了阁下,这给予我很大的幸福” 18。
与主角一起的发现及重获幸福,偶然或者有选择性地阅读及再阅读文学作品,是文学的标准。如同博尔赫斯所认为的,倘若这一愉悦缺席,此书在此刻也将与我们无关。相反,倘若我们获得的这种幸福,作为一个迹象说明:主人公是我们的朋友。
现实与假想之间的友谊
现在,让我们进入关系的议题,假想与现实之间的交织的关系。将友谊视为《堂吉诃德》的核心议题的博尔赫斯,也认为《堂吉诃德》的“要点”在于在塞万提斯“创作”的现实与假设之间出入的合一 19。此一场景为此:理发师和本堂神父在阿隆佐·奇夏亚诺的图书馆中发现了《堂吉诃德》。一页又一页的阅读,令他们发现所阅读的正是自己的经历,如同发生在《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同一故事发生在另一给人共鸣的情节中,堂吉诃德了解他的冒险经历已然被写就,并以某种方式为读者提供了朋友式的建议。
博尔赫斯认为,这一叙事游戏使读者感到,在某些时候,故事的主人公正是他自己。但是,他不仅说这会导致我们的镜子游戏所引起的形而上学的不安,而且,更深层面上,它开启了一扇与堂吉诃德之间的友谊之窗,这份友谊驱使我们成为像他一样的叙事人物(或者更好的表达是:叙事的作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将一分为二,并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我们自己似乎已然成为正在阅读的故事的作者)。
这正是所谓的“元叙事”,我们可以在《堂吉诃德》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不同的形式中,藉着镜子游戏,“作品出现在作品中”,通过作者的角色转换,读者被提醒他所面对的是一部虚拟的作品,并进入这一虚拟与现实之间的问题性关系之中。在《堂吉诃德》以及在博尔赫斯中,所论及的并非仅仅是文学性的问题,因为现实看起来像童话一样充满神秘的维度,童话比所充斥的当日新闻事件更为真实。
《皮埃尔·蒙纳,<堂吉诃德>的作者》
我们已然分享了一些之于友谊,幸福与文学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反思。为了进入对此一关系的深入探讨,现在让我们来分享博尔赫斯的一个故事,并作为所探讨的议题的一个例证,故事名为《皮埃尔·蒙纳,<堂吉诃德>的作者》 20。这一故事是文学批判的典型,并被视为“博尔赫斯的美学宣言”。瓦莱里奥·费利托(Valerio Ferlito)与其他人一起对此进行了肯定,我们可参阅他对这种“美学” 21的详尽分析。此处,我们将重点谈论友谊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但是,首先,有必要对不了解剧情的读者给予一些基本的普及。
剧情
眨眼来看,所描述的剧情十分简单:当法国鲜为人知的作家皮埃尔·蒙纳去世时,他的真朋友们 22渴望为其作品伸张正义,他们认为亨利·巴歇尔女士并未对此给予正当的评价。这些朋友之一——博尔赫斯给予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说皮埃尔·蒙纳有两部作品:其一是“可见的”,由此草拟新表,另一个被认为是“不可见的”,他是唯一的证人,因为皮埃尔·蒙纳的这些作品“不允许被任何人查阅,并有意使之消逝于此世之中” 23。
对于这些不可见的作品的唯一见证是蒙纳写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根据叙述者的声音,这封信写于1934年9月30日。在其中,他描述了其作品的“写作计划”是“简直令人惊异的”。由此接续,“我承担了从字面上重建他的【塞万提斯的】自由创作的作品的神秘责任,即‘创作《堂吉诃德》’” 24。
故事情节的一个重要细节是,这封信并未被我们的叙述者朋友,费力地置于目录列表之中,他指出它们是“容易列举的”。因此,“亨利·巴歇尔女士(Henri Bachelier)的遗漏与补加之罪罪不可赦” 25。皮埃尔·蒙纳先生的古怪的计划与叙述者缺乏科学的可信性,使得故事最终以神秘的方式呈现,如同《堂吉诃德》中所发生的。由此,我们意识到,真实的友谊,作为叙述的核心议题,驱动他将他的秘密付之朋友,朋友则承担起为之辩护,为之讲述的责任。
以上即是我们对于剧情的简要概括(但是,也许我也会做其他的,不同的)。然而,“在这个简单的论证下,隐藏着后现代叙述的元叙述结构的更为复杂性,以及接受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的前置性范例” 26。《皮埃尔·蒙纳,<堂吉诃德>的作者》可以被成千上万次地阅读,并总会由此温故知新——如同反射他人的镜子——开启叙述的新视野与新解释。
序幕
博尔赫斯的“序幕”远近闻名:不论是他为自己的书所撰写的序幕,还是为他人的书所撰写的序幕,以及他的作为“序幕的序幕” 27。它是有关与其他作家互动、并致力于修正的元叙事——有时,这一写作方式意义深远——因为它可向其作家开启新的视域。
在虚构小说的导言中,包含一种引导我们进入剧情的叙述,博尔赫斯给与读者关于他的书中议题的“解释”,他将之定义为“格子”,如同象棋中的格子。其一被成为“警察的格子” ;其另外两处被称为 “想象的性格的格子” ;还有一处被标注为他并非 “叙述的第一作者”; 《圆桩废墟》被解释为叙述的 “一切都是非现实的” ;《皮埃尔,<堂吉诃德>的作者》将非现实定义为“主人公所承担的命运”。进而言之,“我认为他的著作清单不是很有趣,但也不是任意的:这是他的心路历程示意图” 28。
由其最后的陈述所引发的思索,始终令学者们蠢蠢欲动并余味无穷 29。我们不妨将视线集中在一个重要的细节:博尔赫斯并没有将不真实性归因于整个故事,也没有归因于虚构的作者,而是认为,这是“主人公对自己强加的命运”。那么,此处的主人公是谁?他对自己施加了怎样的命运?
通常假设“主角”是皮埃尔·蒙纳,而“他对自己施加的命运”与他的“创作《堂吉诃德》”的“意图”相吻和。但也并非如此。事实上,皮埃尔·蒙纳想“在某种方式上,成为塞万提斯” 30。因此,攸关处为,他有义务“删除《堂吉诃德》的第二部分的自传性导言” 31,尽管人们会忘记,令人着迷的隐含性的结论,即《创作<堂吉诃德>》任务的不可能性。
主人公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谁是叙事的真正的主人公。在一定的意义上,也需要反思,谁是《堂吉诃德》的主角。一些人认为,基于一定的理由,《曼查的堂吉诃德》的主角并非是一位绅士,而是塞万提斯本人。卡洛斯·奥斯卡·纳利姆(Carlos Oscar Nállim)说, “也许我的一位博学之友对于塞万提斯的权宜之计的结尾的解释是深刻的,即将之视为‘不可靠的叙事者’” 32。这一特质是一个很小的技术奇迹,并意味着文学史上首次对于亚里士多德美学原则的冲破,由此论证了叙述者对于信息的无所隐藏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塞万提斯似乎是有意如此,让堂吉诃德告诉桑丘和单身汉卡拉斯科(Carrasco),他将去开去披荆斩棘,开拓新土,并请求他们对此秘密的守口如瓶。此处,塞万提斯提及 “卡拉斯科许诺保守一切诺言” 33。然而,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小说的持续进程中,我们并未被告知这一诺言是否被落实。只有在第二部分的十五章,塞万提斯才使得卡拉斯科张口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以将堂吉诃德驱逐出局,从而击败他——伪装成镜子骑士——,由此除了卷土回家之外,别无选择,既然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将他从其胡言乱语中唤醒。
此处的文学史上的首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将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司空见惯。博尔赫斯在诸多作品中对此有所使用,例如《剑势》( La forma della spada)以及《阿斯特里昂之家》(La casa di Asterione) 34。其要点为:叙述者成为作品的主角。“小说的主人公——纳利姆说——不再局限于剧情中的主角,还可以是叙述者,如同这里【在《堂吉诃德》中】所发生的”。此外,“我十分确定博尔赫斯会赞同这一观点” 35。
叙述者成为主角的事实,使得读者“步入”叙述或者“小说”之中。读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认为”他自己也随之成为主角,尾随不可靠的叙述者的欺骗性的脚步。此时,阅读的审美愉悦在于对小说的“重写”。
在《皮埃尔·蒙纳,<堂吉诃德>》的作者一书中,主人公实则为作者博尔赫斯本人,藉叙述者的口吻,他对加于他的朋友的命运做出解释, 如此使得他的朋友成为可信的,并且,他本人也声称,“这会使得我们对我自己的悲惨命运的辩护更加容易” 36。他对我们的叙述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我们被他的声音所震撼。我们对他过度信任,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去讨论皮埃尔·蒙纳是否真实存在。若无此叙述者,我们将没有关于蒙纳的任何认知,因为他已焚毁其所有的一手资料,这封书信也无法在他的个人档案中获取。正是叙述者“发现”了蒙纳的重要性,他的写作技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阅读《堂吉诃德》的新的可能性,如同蒙纳(跨越了阅读所有的‘错误归因’与‘时空错位’的可能性,如同所定义的)。
叙述以如下的地点和时间结束:“尼姆,1939” 37, 并有如下的注释,其最后一句是“跳跃的篝火”,指皮埃尔·蒙纳对他的文字的所作所为,它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叙述者的声音比书面文字重要,它旨在描述角色之间的友谊,而这些角色将永远成为我们的朋友。
《皮埃尔·蒙纳,<堂吉诃德>的作者》中的友谊
为了佐证如上结论,我们遵循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认为的长胜的轨道。这一轨道由 “友谊”和“朋友”的构成——更确定地说,“我们的朋友”——在叙述的文本中出现了五次。
第一次,当叙述者首次指称“蒙纳的真朋友”时,指那些决定在他的墓穴上修复由于他们的记忆模糊而导致的错误的朋友 38。不仅仅皮埃尔·蒙纳是博尔赫斯所创作的角色,而且还有他的一些“真朋友”,在这些朋友中,叙述者,为了指称蒙纳是朋友,使用“我们的”这一属格,从而自然而然地将读者带入剧情之中。
第二处对于“我们的朋友”的提及发生在,“我们的朋友的一个玩笑,但被【亨利·巴切尔夫人】所误解” 39。在几乎引发人无限思考的博尔赫斯的游戏之外,此处我们只对“友谊”感兴趣。使得亨利·巴切尔女士失信的不仅仅是她的疏忽和添加——此处还有我们的叙述者佐证——,然而,玩笑却并非指称皮埃尔·蒙纳。这表明,此人对蒙纳“一无所知”,因为,只有朋友对他的玩笑心领神会。
在第三次对于“友谊”的提及中,是当我们的叙述者在他的目录下标注了字母“p”,这一目录是“【皮埃尔·蒙纳】对于保禄·瓦莱利(Paul Valéry)的反击”,并且,在双括号中补充道,“我们对瓦莱利的观点的明确反对”。最后说,“我理解,二者之间的古老的友谊不会带来任何风险” 40。其所强调的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友谊作为叙述文学的关键,因为只有在友谊中才可以更为容易地接受:对同一意涵的正向反对的表达。
在第四次的提及中,叙述者说,“我承认:我已惯于想象随之而来的结局【创作《堂吉诃德》的任务】,以及阅读《堂吉诃德》的任务——《堂吉诃德》的全部——如同蒙纳所曾经想过的那样?些许夜晚之前,在浏览第二十六章时,——这是我从未尝试过的——我认识到我们的朋友的风格,以及他的在这一特殊的句子中的声音:“河中的仙女,痛苦以及含情脉脉的艾轲”。这一伦理的形容词以及其他物理形容词,使我想起莎士比亚的诗行,在一个晚上,我们如此讨论:缠头巾的恶惯满营的土耳其人在哪里” 41。辨别其风格与声音是朋友的特权。
最终,最后一次对友谊的谈论,“我反思:在《堂吉诃德》中,一种模糊不清的 ‘结尾‘是令人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些迹象——轻微但并非不可识别——我们的朋友的‘先前的’书写” 42。
因此,对博尔赫斯而言,美好地阅读“羊皮纸手稿”(在其上重新书写)是“在第二个程度上的重新书写,是对某些隐喻的语境重构” 43。美好的文学作品是可以“重写” 的,而 “重读” ,则需要以友谊为钥。
参考文献
- 参见:J. 卡维蒂, «Borges y su sentido de la amistad», 网页:descontexto. blogspot.com/2013/12/borges-y-su-sentido-de-la-amistad-de.html。
- 同上。作为军人的克鲁斯是马丁·费埃奥(Martin Fierro)的主人公朋友,阿根廷同名民族叙事长诗的主人公。
- J. W. 冬尼 (J.W. Dunne, 1875-1949) 是博尔赫斯所崇敬的爱尔兰作家。
- J. L. 博尔赫斯,《时间与J.W.冬尼》,同上,Altre inquisizioni, Milano, Feltrinelli, 2005, 第28页
- 塞万提斯,《曼查的堂吉诃德》,A. 扎尼尼(A. GIANNINI)的意大利文译本,Milano, BUR, 2007, 附博尔赫斯的 “导言” 。
- 卡尔维诺,《为何阅读经典》,MILANO, MONDADORI, 1995, 第13页。
- R. ALIFANO, «El Quijote de Borges», in La Nación, 2005年1月2日。
- 博尔赫斯,«Mi entrañable señor Cervantes», in Revista de Artes y Humanidades UNICA, vol. 6, n. 12, 2005年1月至4月,第221-230页。
- «Entrevista a Jorge Luis Borges en “A fondo” (1976) », in www.youtube. com/watch?v=2gu9l_TqS8I#t=175.489598774。
- 同上
- 塞万提斯,《曼查的堂吉诃德》,参见II, LXXIV, 第667页。
- 对于这一分类,请参见J. M. TORRES TORRES, «Contraposición de la idea de novela en Cervantes y Borges», in Espéculo. Revista de estudios literarios, Università Complutense di Madrid, 2006: 见网页:www.ucm.es/info/especulo/numero33/contrapo.html。
- 参见:R. ALIFANO, «El Quijote de Borges»。
- 参见:J. L. BORGES, «Mi entrañable señor Cervantes»。
- 参见:同上,Textos recobrados 1931-1955, Barcelona, Emecé, 2000, 第252 页。
- 同上。参见:«Mi entrañable señor Cervantes». 一个惊奇的事实:博尔赫斯八岁时,在其家父的图书馆中阅读英文版的《堂吉诃德》。之后,当他重新阅读西班牙语的版本时,他发现其英译本是一个极差的本子。(参见:同上,Un ensayo autobiográfico, Barcelona, Galaxia Gutenberg – Círculo de Lectores – Emecé, 1999)。。
- 参阅第二部分的第22章。在山洞中,堂吉诃德与想象中的骑士蒙特西诺(Montesinos)相遇,此处,象征般地如同塞万提斯小说的原初的神秘性框架,期间它聚合了时间,主体,客体,现实以及梦境。
- 塞万提斯,《曼查的堂吉诃德》,参见., I, XXIV, 第439页。
- 参见:J. L. BORGES, «Mi entrañable señor Cervantes»。
- 参见:同上, Finzioni, Milano, Adelphi, 2014, edizione Kindle。
- V. Ferlito, «Pierre Menard, autore del “Chisciotte” (da “Finzioni” 1944): manifesto dell’estetica di J. L. Borges»,31valfer03.myblog.it/2016/12/21/j-l-borges-pierre-menard-autore-del-chisciotte-riflessioni。
- 在这里,我们回想起本文起初,卡维蒂关于博尔赫斯的“真朋友”的表达。
- 参见:J. L BORGES, Finzioni, edizione Kindle, 第439页。
- 同上,第397页。
- 同上,第310页。
- S. JUAN-NAVARRO, «Atrapados en la galería de los espejos: hacia una poética de la lectura en “Pierre Menard” de Jorge Luis Borges», Clemson, Torres – King, 1989, 第102-108页,请参见网页:www.sjuannavarro.com/files/borgespierremenard.pdf。
- J. L. BORGES, Prologhi: con un prologo ai prologhi, Milano, Adelphi, 2017 (edizione ebook). 在序幕中,博尔赫斯设想了一本书(但并未并写就), “由一系列的序幕所构成的未存在的书”。在其中,“《堂吉诃德》或 《基雅诺》的序幕中,他从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的魔鬼,梦想成为被魔法师包围的一名骑士,或者是一名骑士,被梦想成为一名可怜的魔鬼的魔法师包围”。
- 同上,参见:Finzioni, 第46-49页。
- 在博尔赫斯的之于皮埃尔·蒙纳的“可见著作”清单中,声称为所有的反思奠基,因为这是“他本人的心灵史”与他的“美学”。
- 参见:J. L BORGES, Finzioni, 第377页。
- 同上,第379页。在此处插入的序幕中,塞万提斯游戏般地自我分离,并将自己转变为主角,由此意味着,“在这一【作者】主角,而非蒙纳的角色中呈现<堂吉诃德>”。
- C. O. NÁLLIM «Borges, Cervantes, don Quijote y Alonso Quijano», in Cervantes en las letras argentinas, III, Buenos Aires, Academia argentina de Letras, 1998, 65-81: 参见网页: cvc.cervantes.es/literatura/quijote_america/argentina/nallim.html。
- M. DE CERVANTES, Don Chisciotte della Mancia, cit., II, III, 第347页。
- J. B. AVALLE-ARCE, «Cervantes y el narrador infidente», in Dicenda, Cuadernos de Filología Hispánica, n. 7. Arcadia, Estudios y textos dedicados a Francisco López Estrad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1988, 第164-172页。
- 参见:C. O. NÁLLIM, «Borges, Cervantes, don Quijote y Alonso Quijano
- 参见:J. L BORGES, Finzioni, 第316页。
- 同上,第448页。
- 参见,同上,第313页。
- 同上,第352页,脚注7。此处所涉及的是对于“考维德所做的圣方济·沙雷的《虔敬之路指南》的文字版”的(讽刺性的)指称。
- 同上,第345页。
- 同上,第380-384页。
- 同上,第441页。
- 参见:V. FERLITO, «Pierre Menard…»。